(努尔哈赤)第一章:父祖被杀,靠十三副甲起兵
一、风雪辽东
万历十一年(1583年)正月,辽东的雪下得比往年都大。
建州左卫苏克素护河畔,鹅毛大雪将赫图阿拉城外的山岭覆盖得一片苍茫。北风如刀,刮过女真人聚居的村寨,刮过那些用桦木和泥土垒成的屋舍,在茅草屋顶上发出呜呜的哀鸣。
努尔哈赤站在自家院子的木栅栏旁,望着漫天飞雪,眉头紧锁。
他二十五岁,身材魁梧,肩宽背厚,一张方脸上生着浓密的眉毛和锐利的眼睛。此刻那双眼睛正望着远处官道上隐约可见的明军旗帜,眼神里藏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。
“哥,外头冷,进屋吧。”
身后传来妹妹的声音。努尔哈赤回头,看见同母妹妹穆库什端着热气腾腾的奶茶站在门口,脸上带着担忧。
“阿玛和玛法(祖父)随李总兵出征已有七日,”努尔哈赤接过奶茶,语气低沉,“按理昨日就该回来了。”
“许是被大雪耽搁了。”穆库什宽慰道,但她自己的眼神也透露着不安。
院门被推开,一个少年裹着皮袍冲进来,是努尔哈赤的异母弟弟舒尔哈齐。他十六岁,满脸通红,不知是冻得还是急得。
“大哥!我听寨子里的人说,古勒寨那边出事了!”
努尔哈赤心中一紧:“什么情况?”
“具体不清楚,但有从那边逃回来的兵丁说……说仗打得很惨。”舒尔哈齐喘着粗气,“阿台(阿台,建州女真首领)据守古勒寨顽抗,李总兵(李成梁,明朝辽东总兵)调了重炮轰城……”
话音未落,远处传来马蹄声。
三人都转头望去,只见寨子入口处,几个骑马的兵士踏雪而来,为首的是个穿着明军制式棉甲的传令兵。他们没进寨子,只是在寨门外与守卫交谈几句,递了份文书,便调转马头离去。
守卫是个老族人,拿着文书,脚步沉重地向努尔哈赤家走来。
那一刻,努尔哈赤的心沉了下去。他太熟悉这种场景了——战场上传来消息时,总是这样。
老守卫走到院门前,嘴唇动了动,却没发出声音。他双手颤抖着递上文书,那是一封盖着明军大印的公函。
努尔哈赤接过,展开。
雪落在羊皮纸上,迅速融化成水渍,模糊了字迹。但他还是看清了——
“建州左卫指挥使觉昌安、塔克世,随征古勒寨,于混战中不幸罹难……”
后面的字,努尔哈赤看不清了。
世界仿佛在这一刻静止。雪还在下,风还在吹,但他听不见任何声音,只觉得胸口像是被重锤狠狠砸中,一口气憋在那里,上不来,下不去。
“哥?”穆库什的声音很遥远。
舒尔哈齐抢过文书,看了一眼,脸色瞬间煞白:“不……不可能!阿玛和玛法只是随军助战,怎么会……”
“怎么死的?”努尔哈赤终于开口,声音沙哑得连他自己都陌生。
老守卫低下头:“传令兵说……是攻寨时被误杀。具体情形,要等李总兵的正式文书。”
“误杀?”努尔哈赤重复这个词,突然发出一声冷笑。
那笑声让在场的人都打了个寒颤。
他转身进屋,步伐很稳,甚至没有踉跄。但跟进去的舒尔哈齐看见,兄长背在身后的双手,已经攥成了拳头,指节发白,青筋暴起。
二、血债
三天后,详细消息才陆续传来。
努尔哈赤坐在火炕上,听着族中老人打探来的情报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火盆里的炭火噼啪作响,映着他棱角分明的侧脸。
“古勒寨之战,”说话的是额亦都,努尔哈赤的发小,也是他最信任的伙伴之一,“阿台据险死守,李总兵久攻不下,伤亡惨重。后来是尼堪外兰(尼堪外兰,建州女真图伦城主)献计,说可以劝降。”
“尼堪外兰……”努尔哈赤低声念着这个名字。
“对,他说与寨中守军有旧,愿意去劝降。李总兵允了。”额亦都继续道,“但不知怎的,尼堪外兰进城后,寨门突然大开,明军以为是要投降,一拥而入。结果寨内伏兵四起,明军又退了出来,死伤无数。”
“阿玛和玛法当时在何处?”
“老指挥使(觉昌安)担心孙女(觉昌安的孙女、阿台之妻)安危,带着塔克世大人想趁乱进城救人。结果……正好赶上明军溃退,寨门关闭,他们被困在城下。明军炮火无眼……”
额亦都说不下去了。
屋里一片死寂。
许久,努尔哈赤才问:“尼堪外兰呢?”
“他……他在明军溃退时,带着自己的人马撤出来了,毫发无伤。而且,”额亦都顿了顿,“李总兵似乎很赏识他,据说要扶持他做建州女真的首领。”
舒尔哈齐猛地站起来:“凭什么?!阿玛和玛法是明朝任命的建州左卫指挥使,是朝廷命官!他们为明朝效力而死,明朝不但不给个说法,还要扶持那个可能害死他们的人?”
“小声点!”另一个族人紧张地望向窗外,“隔墙有耳……”
“怕什么!”舒尔哈齐年轻气盛,“难道我们还不能讨个公道了?”
一直沉默的努尔哈赤终于开口:“公道,是要自己去讨的。”
他站起身,高大的身影在墙上投下长长的影子:“准备一下,我要去广宁(明朝辽东总兵驻地)。”
“去广宁做什么?”
“见李总兵。”努尔哈赤的眼神冰冷,“我要亲自问清楚,我父祖是怎么死的。如果是战死沙场,我认。如果是被人陷害……”
他没有说下去,但屋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股杀气。
三、广宁问罪
正月二十七,雪停了,但路更难走了。
努尔哈赤带着舒尔哈齐、额亦都等十余人,骑马赶往广宁。路程三百余里,他们日夜兼程,四天后抵达这座辽东军事重镇。
广宁城高墙厚,城门处明军守卫森严。努尔哈赤递上建州左卫的文书,说明来意,守卫让他们在城外等候传唤。
这一等,就是两天。
第三天下午,终于有军官出来,带他们进城。
总兵府气派非常,朱门高墙,石狮镇守。穿过三重院落,来到正厅前,军官让他们在阶下等候。
厅内传来谈笑声,隐约能听见李成梁洪亮的嗓音,还有另一个谦恭的附和声——那声音努尔哈赤很熟悉,是尼堪外兰。
舒尔哈齐咬紧牙关,额亦都按住他的肩膀。
又过了半个时辰,厅门打开,一个穿着绸缎棉袍的中年男子走出来,正是尼堪外兰。他看见阶下的努尔哈赤,明显愣了一下,随即堆起笑容:
“这不是觉昌安大人的孙子吗?节哀,节哀啊。”
努尔哈赤盯着他,一言不发。
尼堪外兰被他看得有些发毛,干笑两声:“李总兵在里面等着呢,快进去吧。”说完匆匆离去,那模样,竟有些落荒而逃的意味。
进到厅内,暖意扑面而来。
李成梁坐在主位上,年过五旬,但身材魁梧,目光如电,不愧是镇守辽东二十年的名将。他打量着跪下行礼的努尔哈赤,半晌才道:
“起来吧。你父祖的事,本帅已经知道了。”
努尔哈赤起身,垂首而立:“敢问总兵大人,我父祖究竟如何殉难?”
“战阵之上,刀枪无眼。”李成梁语气平淡,“他们随军征讨叛逆阿台,奋勇当先,不幸被流矢炮火所伤,实乃忠烈。朝廷自有抚恤,你回去等着便是。”
“流矢炮火?”努尔哈赤抬起头,“可我听闻,他们是因尼堪外兰诈降之计,被困城下,遭明军炮火误伤。”
李成梁脸色一沉:“战场传言,岂可尽信?尼堪外兰献策有功,本帅已表奏朝廷,将由其暂领建州事务。你年纪尚轻,当好生安抚部众,不要生事。”
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
舒尔哈齐忍不住开口:“总兵大人!我父祖为朝廷效力多年,如今死得不明不白,难道连个说法都没有吗?”
“放肆!”李成梁一拍桌案,“你是在质问本帅?”
厅内侍卫的手按上了刀柄。
努尔哈赤拉住弟弟,再次跪下:“总兵大人息怒,舍弟年轻气盛,口无遮拦。只是父祖横死,为人子者心中悲愤,还请大人体谅。”
李成梁脸色稍缓:“本帅理解你的心情。这样吧,朝廷抚恤之外,本帅再拨二十道敕书(明朝发给女真各部的贸易凭证,可凭此入关贸易)、三十匹马给你,也算补偿。你回去好生过日子,不要胡思乱想。”
“那尼堪外兰……”
“此事已定,无需多言。”李成梁摆摆手,“退下吧。”
从总兵府出来,天色已暗。
舒尔哈齐一拳砸在墙上:“大哥!你就这么忍了?”
“不忍又能如何?”努尔哈赤望着广宁城的街道,灯火渐次亮起,汉人、女真人、蒙古人来来往往,这座城繁华依旧,不会因为两个女真头领的死而有任何改变。
额亦都低声道:“李总兵明显在保尼堪外兰。我打听过了,尼堪外兰答应每年向明朝进贡更多的貂皮、人参,还承诺协助明朝控制女真各部。对李成梁来说,一个听话的傀儡,比忠烈之后更有用。”
“所以阿玛和玛法就白死了?”舒尔哈齐眼睛通红。
努尔哈赤没有回答。
他走到马前,抚摸着马颈,良久才道:“先回去。”
四、十三副遗甲
回到赫图阿拉,已是二月中旬。
族人们围上来,急切地询问结果。当听到李成梁的态度和决定后,人群沉默了。
一种压抑的愤怒在蔓延,但更多的是绝望。
建州左卫如今群龙无首,尼堪外兰有明朝支持,必然会来吞并。到时候,他们这些觉昌安、塔克世的旧部,会是什么下场?
当晚,族中长老齐聚努尔哈赤家。
屋里挤了二十多人,油灯昏暗,映着一张张愁苦的脸。
“努尔哈赤,你是塔克世的长子,你说该怎么办?”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问道。
所有人都看向他。
努尔哈赤坐在火炕上,缓缓扫视众人。这些族人,有些是跟着祖父南征北战的老兵,有些是父亲提拔的将领,还有些是姻亲故旧。此刻,他们的命运都系于自己一身。
“明朝不给我们公道,”他开口,声音不大,但字字清晰,“那我们就自己讨。”
“怎么讨?”有人问,“我们如今兵不过百,甲不过十副,怎么跟尼堪外兰斗?他背后还有明朝……”
“兵少,可以招。甲缺,可以造。”努尔哈赤站起身,走到屋角,掀开一张厚厚的熊皮。
下面是一口樟木箱子。
他打开箱盖,里面整齐地叠放着铠甲——胸甲、背甲、护臂、护腿,虽然有些已经锈蚀,但依然能看出精致的做工。
“这是……”有人认了出来。
“阿玛留下的十三副铠甲。”努尔哈赤抚摸着冰冷的铁甲,“还有祖父传下的宝剑、弓矢。这就是我们的本钱。”
屋里响起吸气声。
十三副甲,听起来少得可怜。但在女真各部,铠甲是极其珍贵的战略物资。明朝严格限制铁器流入辽东,一副完整的铁甲,往往需要几代人积累才能置办。很多小部落的头领,都未必有一副像样的铠甲。
塔克世留下这十三副甲,几乎是他毕生的积蓄。
“凭这十三副甲,我们能做什么?”舒尔哈齐问出了所有人的疑惑。
努尔哈赤从箱中取出一件胸甲,举起来:“这甲,能护住一个人的性命。十三副甲,就能让十三个勇士不畏箭矢,冲锋在前。有了敢冲锋的人,就能带动更多的人。”
他转向众人,眼神灼灼:“我要用这十三副甲起兵,讨伐尼堪外兰,为父祖报仇,夺回建州左卫!”
屋里死一般寂静。
起兵?对抗尼堪外兰,对抗尼堪外兰背后的明朝?这听起来像是疯了。
许久,额亦都第一个站出来:“我跟你干。”
接着是安费扬古,另一个发小:“也算我一个。”
舒尔哈齐自然不用说。
陆陆续续,有七八个年轻人站了出来。他们都是塔克世旧部的子弟,血气方刚,对尼堪外兰早就心怀不满。
但更多的族人低着头,不敢表态。
努尔哈赤理解他们的顾虑。起兵是死路,不起兵也是死路,但至少后者能多活几天。
“我不勉强任何人。”他说,“愿意跟我干的,三天后来这里集合。不愿意的,现在就可以离开,我绝不追究。”
人群陆续散去。
最后屋里只剩下努尔哈赤、舒尔哈齐、额亦都、安费扬古四人。
油灯噼啪一声,爆了个灯花。
“大哥,就我们几个,够吗?”舒尔哈齐问。
“不够。”努尔哈赤诚实地说,“所以我们要招兵。建州各部,不满尼堪外兰投靠明朝的大有人在。苏克素护河一带,还有玛法和阿玛的旧部散居各处。把他们聚拢起来,就是一支力量。”
“可他们凭什么跟我们干?”
“凭这个。”努尔哈赤指了指铠甲,“也凭这个。”
他拔出祖父留下的宝剑,剑身映着火光,寒芒凛冽。
“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,觉昌安的孙子、塔克世的儿子,没有认命,没有屈服。我们在为父祖报仇,在建州女真争一口气!”
五、聚义
接下来的三天,努尔哈赤几乎没有合眼。
他带着额亦都等人,骑马奔走于苏克素护河沿岸的村寨,拜访一个又一个族中老人、旧部将领。
有些人闭门不见,有些人婉言推辞,但也有些人,在听说了广宁之行的结果后,拍案而起。
第四天清晨,努尔哈赤家院外,聚集了八十多人。
他们中,有塔克世的亲兵,有觉昌安的老部下,也有闻讯而来的各路好汉。武器五花八门——腰刀、长矛、猎弓,甚至还有锄头、木棒。但每个人眼中,都有一股火。
努尔哈赤站在台阶上,看着这些人。
八十三人,加上他们兄弟和额亦都等,总共八十八人。
这就是他起兵的全部家当。
“各位!”他开口,声音在清晨的寒风中传得很远,“今天站在这里的,都是我的兄弟!我们为什么聚在一起?因为我们的父兄被尼堪外兰害死,因为明朝不给我们公道,因为有人要骑在我们建州女真头上拉屎撒尿!”
人群骚动,有人喊:“说得对!”
“尼堪外兰是个什么东西?”努尔哈赤提高声音,“他原本只是图伦城一个小头领,靠着巴结明朝,陷害同族,如今想当建州之主?他配吗?”
“不配!”众人齐吼。
“李成梁以为,给点敕书、马匹,就能让我们忘了杀父之仇?他以为扶持一个听话的狗,就能让建州女真永远跪着?”努尔哈赤抽出宝剑,直指苍穹,“我今天告诉各位,也告诉所有女真人——我们不是狗!我们是山林里的虎,是草原上的鹰!我们的命,要自己挣!我们的仇,要自己报!”
“报仇!报仇!报仇!”
呐喊声震天响,惊起了林中的飞鸟。
努尔哈赤举起手,众人安静下来。
“八十八个人,很少。十三副甲,很少。”他看着每一张脸,“但我们的心是齐的!我们的血是热的!今天,我努尔哈赤对天发誓:必诛尼堪外兰,为父祖报仇!必兴建州女真,让我们的子孙不再任人欺辱!若违此誓,天诛地灭!”
“誓死追随!”额亦都单膝跪地。
紧接着,安费扬古、舒尔哈齐,以及所有八十八人,全部跪下。
那一刻,努尔哈赤知道,没有回头路了。
六、首战图伦
第一个目标,是尼堪外兰的老巢——图伦城。
图伦城位于苏克素护河下游,距赫图阿拉约一百二十里。城池不大,但墙高壕深,易守难攻。尼堪外兰的主力虽不在城中,但留守的也有三四百人。
努尔哈赤的八十八人,要攻下这座城,听起来像是痴人说梦。
但他有他的办法。
起兵后的第五天,努尔哈赤率队出发。他们没有走大路,而是穿山越岭,走猎人小道,昼伏夜出。队伍中多是本地人,熟悉地形,行动迅速。
二月底,他们抵达图伦城外十里的一片密林。
努尔哈赤派额亦都带几个机灵的手下,扮作猎户进城打探。傍晚时分,额亦都回来了。
“城里守备松懈。”他报告,“尼堪外兰带主力去了抚顺,说是要跟明朝官员会谈。留守的头领叫巴尔达,是个草包,整天喝酒玩女人。守军大概三百人,分驻四门,夜里有一半会溜出去赌钱。”
“城门守卫如何?”
“南门最松,守门的是巴尔达的侄子,不到天黑就锁门睡觉。”
努尔哈赤沉思片刻,有了计划。
当晚子时,图伦城南门外。
两个守门的兵丁正靠着城墙打瞌睡,突然听到草丛里有动静。
“谁?”一个兵丁警觉地举起长矛。
草丛里钻出个人,穿着破皮袄,满脸堆笑:“军爷,是我,山里打猎的,迷路了……”
“滚远点!城门关了!”
“军爷行行好,让我进去吧,外头有狼……”
“说了不行就不行!”兵丁不耐烦地推搡。
就在这时,黑暗中突然窜出几个人影,捂嘴的捂嘴,抹脖子的抹脖子,两个守门兵丁还没来得及出声,就软倒在地。
努尔哈赤从阴影中走出,挥了挥手。
八十八人如幽灵般涌入城门。
城内静悄悄的,大多数人都已熟睡。努尔哈赤兵分三路:一路由额亦都率领,直扑兵营;一路由安费扬古率领,控制粮仓武库;他自己带主力,杀向城主府。
城主府里,巴尔达正搂着两个女人喝酒,听到外面骚动,醉醺醺地骂:“吵什么吵!”
话音刚落,大门被踹开。
努尔哈赤提剑而入,剑尖滴血。
巴尔达酒醒了一半,慌忙去抓墙上的刀,但已经晚了。额亦都的刀架在了他脖子上。
“好汉饶命!饶命啊!”巴尔达瘫软在地。
“尼堪外兰在哪?”努尔哈赤问。
“去、去抚顺了……明天……明天才回来……”
努尔哈赤点点头:“绑起来。”
战斗结束得很快。守军群龙无首,又是在睡梦中被突袭,大部分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就做了俘虏。少数抵抗的,也被迅速解决。
天亮时,图伦城头换上了觉昌安家族的旗帜。
努尔哈赤站在城楼上,望着初升的太阳,心中没有丝毫喜悦。
这只是第一步。
他知道,尼堪外兰很快就会反扑,明朝也可能介入。他必须在这之前,壮大自己。
“大哥,俘虏怎么处理?”舒尔哈齐问。
“愿意归顺的,收编。不愿意的,放走。”
“放走?”舒尔哈齐不解,“那不是纵虎归山?”
“我们人手太少,关不住这么多人。”努尔哈赤说,“而且,放他们走,消息才能传出去。我要让所有人知道,我努尔哈赤起兵了,打下了图伦城。”
他转身,对额亦都说:“清点缴获,开仓放粮。城里百姓,每户发三斗米。”
“这……”额亦都犹豫,“我们的粮食也不多。”
“照做。”努尔哈赤语气坚决,“要让人跟我们,就得先让人吃饱。”
事实证明,这个决定是明智的。
图伦城百姓原本对尼堪外兰的统治就心怀不满,如今见新来的头领不仅不抢掠,还开仓放粮,态度立刻转变。当天就有几十个青壮年表示愿意投军。
更让努尔哈赤没想到的是,附近一些小部落听说他起兵的消息,也派来使者,表示愿意结盟。
短短三天,他的队伍从八十八人膨胀到三百余人。
虽然大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,但至少,有了个像样的开局。
七、血战兆佳
尼堪外兰的反应比预想中更快。
三月初,他率领两千兵马,从抚顺杀回,直扑图伦城。
消息传来时,努尔哈赤正在校场练兵。
“两千对三百,”额亦都脸色凝重,“这仗没法打。”
“城是守不住的。”努尔哈赤很清醒,“图伦城防本就不固,我们又没时间加固。守城,死路一条。”
“那怎么办?撤?”
“撤,但要撤得有价值。”努尔哈赤眼中闪过一丝精光,“传令下去,收拾粮草物资,今夜撤离。但走之前,给尼堪外兰留点礼物。”
当晚,图伦城燃起大火。
努尔哈赤带着部队和愿意跟随的百姓,撤往苏克素护河上游的密林。他们在那里有个临时营地,是起兵前就准备好的。
尼堪外兰扑了个空,只得到一座空城和满街的灰烬。暴怒之下,他纵兵劫掠了附近几个村寨,然后率军追击。
但山林是努尔哈赤的主场。
他利用地形,不断设伏袭扰,今天吃掉十几个斥候,明天烧掉一批粮草。尼堪外兰的大军在山里转了一个月,人困马乏,连努尔哈赤主力的影子都没摸到。
四月初,尼堪外兰不得不退回图伦城。
他以为努尔哈赤已经逃远,却没想到,这正中了努尔哈赤的下怀。
“尼堪外兰以为我们怕了,”营地中,努尔哈赤对众将说,“实际上,我们在等他松懈。现在他的主力分散各地弹压,图伦城又空虚了。”
“还要打图伦?”舒尔哈齐问。
“不,打兆佳城。”努尔哈赤指向地图上的另一个点,“兆佳城主李岱,是尼堪外兰的姻亲,也是他的铁杆支持者。打下兆佳,就等于断了尼堪外兰一臂。”
“可兆佳城比图伦还坚固,我们只有四百人……”
“所以不能强攻。”努尔哈赤笑了,“得用计。”
四月中旬,兆佳城外来了个商队。
领队的是安费扬古,他扮作皮货商人,带着十几辆大车,说是从蒙古来的。守城兵丁检查车辆,确实都是皮货,便放他们进城。
商队在城里最好的客栈住下,出手阔绰,很快就跟守军混熟了。
三天后的深夜,兆佳城南门突然起火。
守军慌忙救火,混乱中,城门被悄悄打开。早已埋伏在城外的努尔哈赤主力一拥而入。
李岱从睡梦中惊醒,来不及披甲,提刀迎战,正撞上努尔哈赤。
两人在府中庭院厮杀。李岱是沙场老将,刀法凶狠,但努尔哈赤年轻力壮,又怀着血仇,招招搏命。三十回合后,李岱力竭,被努尔哈赤一刀劈中肩膀,倒地被擒。
城主被俘,守军士气崩溃,纷纷投降。
天亮时,兆佳城易主。
这一次,努尔哈赤没有放走俘虏。他将李岱和他的亲信全部处斩,首级悬挂城门示众。消息传出,震动建州。
尼堪外兰大怒,再次率军来攻。
但这一次,努尔哈赤不跑了。
他整合兆佳城的降兵,兵力达到八百人,虽然仍处劣势,但有一战之力。
两军在兆佳城外十里处的山谷相遇。
这是努尔哈赤起兵后的第一场正面会战。
八、山谷血战
山谷狭窄,两侧是陡峭的山坡。
努尔哈赤将主力埋伏在山坡林中,只派两百人正面诱敌。
尼堪外兰率一千五百人抵达,见对方兵少,轻敌冒进,率军冲入山谷。
待敌军完全进入伏击圈,努尔哈赤一声令下,山坡上箭如雨下。
尼堪外兰军顿时大乱。
但此人能得李成梁赏识,确有过人之处。他很快稳住阵脚,命令盾牌手结阵防御,弓箭手还击,同时派骑兵冲击山坡。
战斗进入白热化。
努尔哈赤身披祖父留下的重甲,手持长刀,亲率精锐从山坡杀下,直取尼堪外兰中军。
“尼堪外兰!纳命来!”
他的吼声如雷霆,所过之处,人仰马翻。
尼堪外兰看见他,眼中闪过惧色,但随即被羞怒取代。他也是久经沙场,岂能在一个后生面前退缩?
“小儿狂妄!”
两人在乱军中相遇。
刀剑相击,火花四溅。
这是血仇的对决,没有试探,没有保留,每一招都是搏命。
努尔哈赤的刀法是在山林中与猛兽搏杀练出来的,没有花哨,只有狠辣。尼堪外兰的剑术则是中原名师传授,精妙严谨。
三十回合不分胜负。
但战场的天平在倾斜。
努尔哈赤的部队虽然人少,但士气高昂,又是伏击方,渐渐占据上风。尼堪外兰的部队则开始溃散。
一个亲兵冲到尼堪外兰身边:“大人!顶不住了!撤吧!”
尼堪外兰咬牙,虚晃一剑,拨马便走。
“哪里走!”努尔哈赤紧追不舍。
但就在这时,侧翼突然杀出一支骑兵——是尼堪外兰预留的后队,约三百人,此刻赶来接应。
额亦都见状,急率一队人马拦住追兵:“大哥!穷寇莫追!”
努尔哈赤勒住马,看着尼堪外兰在亲兵护卫下远去,恨恨地一刀劈在地上。
这一仗,尼堪外兰损失近半,元气大伤。努尔哈赤虽然获胜,但也伤亡两百余人,无力追击。
双方暂时进入对峙。
九、艰难的抉择
万历十一年(1583年)秋,努尔哈赤已经控制了苏克素护河上游的大片区域,麾下兵力达到一千二百人。
但他面临的困境越来越严重。
首先是粮食。养活这么多兵,需要海量的粮草。虽然缴获了一些,但坐吃山空。
其次是明朝的压力。李成梁多次派人传话,要求他停止“叛乱”,归顺朝廷。虽然没有直接派兵,但停止了与他的所有贸易,敕书、铁器、盐茶,全部断绝。
最要命的是内部。一些部落见他势大,表面上归顺,暗地里却与尼堪外兰勾结。就在上月,一个刚归附的小头领企图在酒宴上刺杀他,幸亏额亦都机警,才未得逞。
营帐中,油灯昏黄。
努尔哈赤独自坐着,面前摊着一张简陋的辽东地图。
他已经三天没怎么合眼了。
“大哥。”舒尔哈齐端着热汤进来,“喝点吧。”
努尔哈赤接过,没喝,只是盯着地图。
“你在想什么?”
“在想,我们走错路了。”努尔哈赤缓缓道,“这半年,我们东征西讨,打下了不少地盘,但敌人却越来越多。尼堪外兰没死,明朝视我们为眼中钉,连女真各部也把我们当祸害。”
舒尔哈齐沉默。他知道大哥说的是事实。
“我们太急了。”努尔哈赤继续说,“以为凭着血勇,就能报仇雪恨。但打仗不是拼命,是拼实力。我们的实力,还差得远。”
“那怎么办?难道要向明朝低头?”
“不。”努尔哈赤眼神坚定,“仇一定要报,但不是现在。”
他站起身,走到帐外。
秋夜的星空格外明亮,银河横贯天际。
“从明天起,我们停止扩张,巩固现有地盘。”他说,“练兵、屯田、冶铁、造船。我们要把苏克素护河变成铁打的根基。至于尼堪外兰……”
他望向东南方向,那是图伦城所在。
“让他多活几年。但总有一天,我会亲手砍下他的头,祭奠阿玛和玛法。”
十、蛰伏与积蓄
万历十二年(1584年)到万历十三年(1585年),是努尔哈赤起兵后最艰难的两年。
他放弃了快速复仇的幻想,转而埋头经营根据地。
在赫图阿拉旧址,他筑起新城墙,修建房舍、粮仓、武库。组织士兵开垦荒地,种植粟米、高粱。派人深入长白山,采集人参、貂皮,通过蒙古商人走私到关内,换取急需的铁器、布匹、食盐。
他还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——主动向明朝示好。
万历十三年春,他派舒尔哈齐带着厚礼前往广宁,求见李成梁。
舒尔哈齐回来时,带回了二十道敕书和一份承诺:只要努尔哈赤不再攻击尼堪外兰,明朝可以承认他对现有地盘的控制。
“大哥,李成梁这老狐狸,明显是在用缓兵之计。”舒尔哈齐愤愤道。
“我知道。”努尔哈赤平静地说,“但我们需要时间。有了这二十道敕书,我们就能合法贸易,换回粮食铁器。等我们强大了,再撕破脸也不迟。”
“可族里很多人不理解,说你忘了血仇……”
“让他们说去。”努尔哈赤望向窗外,练兵场上,士兵们正在操练,“真正的仇恨,不是挂在嘴上,是记在心里,用在手上。”
这两年,他不仅积蓄物质力量,更在培养人才。
额亦都、安费扬古、费英东(后来投奔的猛将)……一个个年轻将领在他麾下成长起来。他创立了简单的军制,以牛录(三百人为一牛录)为单位,设牛录额真(长官)统领。虽然简陋,但比之前的一盘散沙强多了。
更重要的是,他赢得了人心。
苏克素护河的百姓发现,这个新头领与其他女真首领不同:他不滥杀,不劫掠,分田分地,鼓励生产。虽然税赋不轻,但至少能让人看到希望。
越来越多的人投奔而来。
到万历十三年底,努尔哈赤麾下已有五个牛录,一千五百精兵,控制着苏克素护河沿岸三百里地。
而尼堪外兰,这两年也没闲着。
他依靠明朝支持,不断吞并周边小部落,势力扩张到浑河流域。两人虽然暂时停战,但都知道,决战迟早会来。
万历十四年(1586年)春,一个消息传来,打破了短暂的平静。
十一、最后的通牒
“尼堪外兰去了抚顺关,向明朝请求庇护。”
营帐中,额亦都报告最新情报。
努尔哈赤皱眉:“什么意思?”
“据说他收到风声,知道我们这两年实力大增,怕我们报复,所以想躲进明朝控制的抚顺城。”
“李成梁答应了?”
“暂时还没有,但很可能答应。”额亦都说,“尼堪外兰这几年帮明朝控制女真各部,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明朝保他,也在情理之中。”
帐内众将都看向努尔哈赤。
如果尼堪外兰真的躲进抚顺城,那就麻烦了。抚顺是明朝在辽东的重要边关,有重兵把守。努尔哈赤再大胆,也不敢公然攻击明朝城池。
“大哥,怎么办?”舒尔哈齐问。
努尔哈赤沉思良久,突然笑了。
那笑容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。
“他以为躲进抚顺就安全了?”努尔哈赤站起身,“传令,集结所有兵马,我们去抚顺。”
“攻打抚顺?”安费扬古大惊。
“不,我们去要人。”努尔哈赤眼神锐利,“去告诉明朝守将,要么交出尼堪外兰,要么……我们就自己进去拿。”
“这太冒险了!万一明朝翻脸……”
“他们不会。”努尔哈赤自信地说,“李成梁是个聪明人。为了一个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尼堪外兰,跟我们开战,不值得。”
他走到地图前,指着抚顺的位置:“而且,我了解明朝那些边将。他们最怕的不是打仗,是麻烦。我们把大军开到抚顺城下,摆出不惜一战的架势,他们会怎么选?”
众人明白了。
这是赌博,赌明朝不愿意为了尼堪外兰大动干戈。
“可如果赌输了呢?”费英东问。
“那就打。”努尔哈赤斩钉截铁,“三年的准备,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?尼堪外兰必须死,父祖的仇必须报。哪怕与明朝为敌,也在所不惜!”
帐内安静片刻,随即爆发出整齐的吼声:
“战!战!战!”
十二、兵临城下
万历十四年(1586年)四月,努尔哈赤亲率两千兵马,抵达抚顺关外。
消息传来,抚顺守将王守备大惊失色。
他一边紧闭城门,一边快马向广宁求援。
城下,努尔哈赤扎下营寨,却不进攻,只是派使者送信进城。
信很简单:交出尼堪外兰,我军即退。否则,破城之日,鸡犬不留。
王守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尼堪外兰确实在城里,是三天前带着几十个亲兵逃来的,说努尔哈赤要杀他,求明朝庇护。
当时王守备没多想就收留了——毕竟尼堪外兰是明朝扶持的代理人,保他是分内之事。
可没想到,努尔哈赤这么大胆,敢直接兵临城下要人。
“大人,怎么办?”副将问。
“还能怎么办?守城待援!”王守备擦着汗,“广宁的援军最快也要三天才能到。我们城中只有八百守军,必须撑住。”
“可……努尔哈赤有两千人,而且都是能征善战的女真兵……”
“闭嘴!”王守备怒道,“长他人志气,灭自己威风!抚顺城墙高大,他攻不进来!”
话虽如此,他心里也没底。
城外的女真军营井然有序,旗帜鲜明,一看就是精兵。反观自己手下这些兵,多年没打过仗,早就废了。
更麻烦的是,城里百姓开始恐慌。有人传言,努尔哈赤只杀尼堪外兰,不伤百姓。不少富户暗中串联,想逼他交人。
内外交困。
第二天,努尔哈赤又派使者来,这次带来了一份礼物——一百张貂皮,十根老山参。
“我家主人说了,只要交出尼堪外兰,这些是谢礼。另外,每年向抚顺关进贡翻倍。”使者语气恭敬,但话里的威胁谁都听得出来。
王守备动摇了。
是啊,为了一个尼堪外兰,值得吗?
此人已经失势,建州女真现在是努尔哈赤的天下。与其保一个废人,不如跟新霸主搞好关系……
但他又不敢擅自做主,毕竟尼堪外兰是李总兵点名要保的人。
正犹豫间,亲兵来报:“大人!广宁来人了!”
王守备大喜,以为是援军,急忙出迎。
来的却只是一个文官,带着李成梁的手令。
手令上只有一句话:“尼堪外兰之事,抚顺守军不得插手,由其自决。”
王守备愣了半晌,突然明白了。
李成梁这是在甩锅。
“自决”?怎么自决?明摆着是让他自己看着办,但出了事,责任也是他的。
文官还低声补充:“总兵大人说了,辽东大局为重。”
大局……什么大局?
王守备苦笑着送走文官,回到府中,看着那份手令,长叹一声。
“去,请尼堪外兰大人过来。”
十三、血仇得报
尼堪外兰来到守备府时,还抱着一线希望。
“王大人,可是广宁援军到了?”
王守备看着他,眼神复杂:“尼堪大人,请坐。”
尼堪外兰坐下,感觉气氛不对:“王大人,怎么了?”
“努尔哈赤在城外,你知道吧?”
“知道……但他不敢攻城!明朝天威……”
“他敢。”王守备打断他,“李总兵的手令来了,说此事由你自决。”
尼堪外兰脸色刷地白了:“自、自决?什么意思?”
“意思是,总兵大人不管了。”王守备摊手,“你可以选择出城与努尔哈赤决战,也可以选择……其他出路。”
“其他出路?”尼堪外兰站起来,声音颤抖,“王大人!我为明朝效力多年!你不能见死不救!”
“我也没办法。”王守备无奈,“城中兵力不足,援军无期。努尔哈赤扬言,不交人就攻城。到时候城破,死的就不止你一个了。”
尼堪外兰瘫坐在椅子上。
他明白了,自己被抛弃了。
就像当年他抛弃觉昌安、塔克世一样,现在明朝抛弃了他。
报应,真是报应。
“王大人,”他嘶哑着嗓子,“如果我出城……你能保我家人平安吗?”
王守备点头:“只要他们留在城里,我保他们无事。”
尼堪外兰惨笑:“好……好……”
他起身,踉踉跄跄走出守备府。
回到住处,他对亲兵说:“备马,出城。”
“大人!城外都是努尔哈赤的人!”
“我知道。”尼堪外兰穿上最好的铠甲,佩上宝剑,“但我尼堪外兰,好歹也是一方首领。要死,也得死在战场上,不能像狗一样躲在城里等死。”
亲兵们面面相觑,最终有十几个人愿意跟他出城。
城门缓缓打开。
尼堪外兰一马当先,冲出抚顺关。
城外,努尔哈赤早已列阵等候。
看见尼堪外兰出来,他眼中闪过一丝意外,随即化为冰冷的杀意。
三年了。
从父祖被杀,到今天,整整三年。
这三年,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一刻。
“尼堪外兰!”努尔哈赤策马出阵,“你还敢出来!”
尼堪外兰勒住马,看着对面那个年轻人。
三年前,他还是个无兵无权的部落小子。如今,已是统率两千雄兵的霸主。
时间,真是个奇妙的东西。
“努尔哈赤,”尼堪外兰开口,“成王败寇,我认了。但我想知道一件事——你父祖的死,真的全怪我吗?”
“不怪你怪谁?”
“怪这个世道。”尼堪外兰苦笑,“女真各部互相攻伐,明朝坐收渔利。我们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,今天你杀我,明天他杀你。你祖父、父亲是如此,我也是如此。”
努尔哈赤沉默片刻,道:“你说得对。但这个仇,我必须报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尼堪外兰拔出剑,“那就来吧。让我看看,觉昌安的孙子,到底有多大本事。”
没有废话,两人策马冲向对方。
这是三年前那场未完决斗的延续。
但这一次,结局早已注定。
尼堪外兰老了,累了,心气已散。而努尔哈赤正值巅峰,血仇在胸,气势如虹。
十回合,尼堪外兰的剑被震飞。
二十回合,他被努尔哈赤一刀劈下马。
摔在地上时,他听见努尔哈赤说:“这一刀,是替我玛法砍的。”
然后是第二刀:“这一刀,是替我阿玛砍的。”
第三刀落下时,尼堪外兰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。
他望着辽东的天空,那么蓝,那么远。
恍惚间,他想起很多年前,和觉昌安、塔克世一起喝酒打猎的日子。那时候,他们还是兄弟,还没被明朝分化,还没被野心吞噬……
可惜,回不去了。
鲜血从喉咙涌出,尼堪外兰用最后的气力说:“努尔哈赤……小心……明朝……”
话没说完,气息已绝。
努尔哈赤站在尸体旁,手中的刀滴着血。
大仇得报,但他心里没有想象中的畅快,只有一种空落落的疲惫。
三年奔波,无数厮杀,就为了这一刻。
值得吗?
他抬起头,望向抚顺城墙。城头上,明朝守军静静看着,没有动作,没有声音。
那一刻,努尔哈赤明白了尼堪外兰临死前的话。
明朝,才是真正的敌人。女真人之间的厮杀,不过是他们操控的游戏。
但今天,游戏规则变了。
他擦干刀上的血,翻身上马,对全军高呼:
“尼堪外兰已死!父祖之仇已报!”
两千将士齐声呐喊,声震四野。
努尔哈赤调转马头,最后看了一眼抚顺关,然后率军离去。
他没有进城,没有挑衅明朝。
因为他还不够强大。
但这一天不会太远。
总有一天,他会回来,不是以乞求者的身份,而是以征服者的姿态。
回师途中,努尔哈赤下令在尼堪外兰伏诛处立碑,上书:
“建州左卫指挥使觉昌安、塔克世殉难处。其孙、子努尔哈赤,于此诛仇敌尼堪外兰,以祭先灵。”
碑立好后,他亲自洒酒祭奠。
酒洒在地上,渗入泥土,仿佛父祖的鲜血。
“阿玛,玛法,”努尔哈赤低语,“仇报了。但路,才刚开始。”
风吹过原野,扬起他的披风。
身后,两千将士肃立,鸦雀无声。
前方,是茫茫的辽东大地,和不可知的未来。
但努尔哈赤知道,从今天起,建州女真的历史,将由他书写。
而他笔下的第一个字,是“血”。
第二个字,是“火”。
第三个字……是“天下”。
发表评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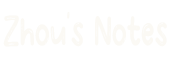





暂时没有评论,来抢沙发吧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