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努尔哈赤)第七章:再迁盛京,稳住内外局面
一、广宁城头的血色晚霞
天命八年(1623年)深秋,广宁城的血腥味还没有完全散去。
努尔哈赤站在城楼之上,望着城西那一片新起的坟茔。那里埋着三个月前因反抗“剃发令”而被处死的三百多名汉人读书人。秋风扫过坟头枯草,发出呜咽般的声响,像是那些亡灵在控诉。
“大汗,风大了。”范文程将一件貂皮大氅披在努尔哈赤肩上。
这位汉人谋士今年四十有二,鬓角已见微霜。三年前他献策取广宁,如今却要面对广宁治理的烂摊子,心中五味杂陈。
“范先生,”努尔哈赤没有回头,声音低沉,“你说,我是不是做错了?”
范文程心中一凛。这是努尔哈赤第一次在他面前表露自我怀疑。
“大汗指的是……”
“剃发易服。”努尔哈赤转过身,六十四岁的脸上刻满风霜,但那双眼睛依旧锐利如鹰,“这三个月,辽东各处因此死者已逾千人。反抗没有停止,反而愈演愈烈。”
范文程沉默片刻,谨慎措辞:“大汗,治大国如烹小鲜。汉人讲‘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’,剃发对他们而言,确是奇耻大辱。但……”他顿了顿,“但若此时退让,则前功尽弃。那些人会说:看,蛮夷到底怕了我们。”
“所以只能硬到底?”
“不。”范文程摇头,“硬要硬得有技巧。学生以为,可以分而治之。”
“说下去。”
“反抗最烈者是读书人和原明朝官吏。这些人有气节,有号召力,必须严厉打击。但普通百姓,所求不过是活命吃饭。可以适当放宽:老人可以不剃发,妇女可以不改服。同时,对那些主动剃发易服者给予奖励——减赋税、分田地。”
努尔哈赤盯着范文程看了许久,突然笑了:“范先生,你这计策,既狠毒又精明。打压头面人物,拉拢底层百姓……这是分化瓦解之道啊。”
“大汗明鉴。”
“那就照你说的办。”努尔哈赤走下城楼,“传令:六十岁以上老人、十岁以下孩童,可不剃发。主动剃发者,赋税减半。再反抗者……杀无赦。”
令下如山,血流成河。
但这次,流血的同时,也有妥协。许多贫苦汉民为了活命、为了减税,选择了屈服。辽东的局势,在血腥镇压与利益诱惑的双重作用下,暂时稳定下来。
可努尔哈赤知道,这稳定脆弱如冰。
二、辽阳城的困局
天命九年(1624年)正月,辽阳。
这座曾经的辽东首府,如今是后金的都城。但城中的气氛异常压抑。女真贵族住在原先明朝官员的府邸里,汉人百姓则被赶到城西拥挤的“民屯区”。每到夜晚,宵禁的鼓声敲响,街道上除了巡逻的八旗兵,空无一人。
正月初八的朝会上,矛盾爆发了。
五大臣之一的扈尔汉——这位跟随努尔哈赤四十年的老将,当着满朝文武的面,痛斥新任户部承政(尚书)恩格德尔。
“这个蒙古人懂什么治国?他推行的‘计丁授田’,把我们女真人都坑惨了!”扈尔汉须发皆张,“我家有三十丁,按令该授田九百亩。可分的都是什么地?要么是盐碱地,要么是山坡地!汉人分的却是肥沃的水浇地!这是什么道理?”
恩格德尔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,去年归顺后金,因通晓汉、蒙、满三种语言,被努尔哈赤破格提拔。此刻他面色涨红,强辩道:“扈尔汉大人,分田是按丁数,不是按身份!况且您那些地虽然贫瘠,但面积大啊……”
“面积大顶什么用?种不出粮食!”扈尔汉转向努尔哈赤,“大汗,这些汉官、蒙官,根本不懂我们女真人的难处!让他们治国,国将不国!”
这话引起了共鸣。许多女真贵族纷纷附和。
努尔哈赤坐在龙椅上,面无表情。他知道,这不只是土地分配问题,更是权力斗争。老牌女真贵族不满新人(特别是非女真人)进入权力核心,借题发挥。
“够了。”他开口,声音不大,但全场肃静。
“土地分配不均,可以调整。但我要问在座各位:你们家中真只有三十丁吗?”努尔哈赤锐利的目光扫过众人,“据我所知,有些人家明明有上百壮丁,却只报二三十。多出来的丁口,要么隐瞒不报,要么充作包衣(家奴)。这样一来,分的田自然不够。”
众人低头,不敢接话。
“从明天起,户部重新清查丁口。隐瞒者,田产充公。至于土地好坏……”他顿了顿,“确实该调整。恩格德尔。”
“臣在。”
“你制定一个新方案:女真人与汉人混编分田,好坏搭配。另外,开垦荒地者,五年免税。”
“遵旨。”
这场风波暂时平息,但努尔哈赤心中警铃大作。
他回到后宫(原明朝经略府内院改建),疲惫地靠在榻上。大妃阿巴亥(乌拉那拉氏,多尔衮生母)端来参茶,轻声问:“大汗今日朝会不顺?”
“何止不顺。”努尔哈赤苦笑,“老臣不满新人,女真不满汉蒙,辽东汉人又心怀怨恨……这江山,比打江山时还难坐。”
阿巴亥二十有八,是努尔哈赤晚年最宠爱的妃子。她聪慧机敏,常能说出些独特见解。
“妾身听说,辽阳城原本有‘四门八关’,易守难攻。可如今看来,这城池格局太小,宫殿简陋,配不上大汗的威仪。”
这话说到了努尔哈赤心里。
辽阳虽是辽东重镇,但毕竟是明朝修建的城池,格局拘谨。后金朝廷挤在原先的经略府内,连个像样的朝会大殿都没有。
更重要的是,辽阳城中汉人太多,占了七成以上。虽然严加管控,但终究是个隐患。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“迁都。”阿巴亥大胆说出这两个字,“迁到一座新城,按我们女真的规矩修建。这样,既能彰显国威,又能摆脱旧朝影响。”
努尔哈赤眼中闪过思索的光。
迁都,他不是没想过。实际上,这两年他一直在考察辽东各处:抚顺太小,沈阳残破,广宁偏远……都不合适。
“你觉得哪里好?”
“沈阳。”阿巴亥说,“沈阳虽遭战火,但根基尚在。它位于辽河平原中心,四通八达。而且……离赫图阿拉更近些。”
离赫图阿拉近,就意味着离女真的龙兴之地近。这个理由,足以说服那些怀旧的老臣。
努尔哈赤陷入沉思。
三、沈阳的抉择
正月十五,元宵节。按汉人习俗,该是张灯结彩的日子。但辽阳城中一片死寂——剃发令下,汉人连过节的心情都没有了。
努尔哈赤却在这天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:巡视沈阳。
名义上是巡视,实际上是考察迁都的可能性。
正月二十,努尔哈赤率众臣抵达沈阳。这座三年前被战火摧毁的城池,如今已部分恢复。后金在此设“盛京将军”,驻兵五千,管理周边。
站在沈阳残破的城墙上,努尔哈赤心中感慨。
三年前,贺世贤在此战死。那是个硬骨头,可惜跟错了主子。
“大汗请看,”新任盛京将军图尔格(额亦都之子)指着城外,“沈阳有‘四塔’之利:东塔镇青龙,西塔压白虎,南塔锁朱雀,北塔守玄武。这是风水宝地啊!”
这话有奉承成分,但沈阳的地理位置确实优越:它位于辽河、浑河之间,土地肥沃;向东可控建州旧地,向西可图辽西,向南威慑朝鲜,向北联络蒙古。
更重要的是,经过战乱,沈阳汉人大量逃亡,如今城中女真人已占多数。在这里建都,民族矛盾会小得多。
“传令:召集工匠,我要重建沈阳。”努尔哈赤做了决定,“不是修补,是重建——按国都的规格。”
这个命令,震惊了随行众臣。
五大臣中,额亦都、安费扬古支持——他们早就觉得辽阳憋屈;费英东、何和礼反对——担心耗费巨大;扈尔汉犹豫——他刚在辽阳置了产业。
回辽阳的路上,反对声不断。
“大汗,重建沈阳至少要三年,耗费百万银两。现在国库空虚,辽东未稳,是不是太急了?”
“辽阳经营三年,刚有起色,现在放弃,前功尽弃啊!”
“沈阳残破,重建期间,大汗驻跸何处?安全如何保障?”
努尔哈赤的回应很简单:“正因为辽东未稳,才要迁都。辽阳是汉人之城,我们住得不安稳。沈阳虽残破,但是白纸一张,正好画我们自己的图。”
他顿了顿:“至于耗费……取之于明,用之于明。广宁、辽阳的库银,还没用完吧?”
这话堵住了众人的嘴。确实,攻占辽东各城,缴获的白银超过三百万两。
迁都之事,就此定下。
但努尔哈赤没想到,这个决定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。
四、舒尔哈齐的最后机会
消息传到赫图阿拉时,舒尔哈齐正在病中。
这位曾经的后金第二号人物,如今只是个被边缘化的“和硕贝勒”。三年前被调回建州旧地,名义上是镇守龙兴之地,实则是远离权力中心。
“迁都沈阳……”舒尔哈齐靠在病榻上,脸色蜡黄,“大哥这是要彻底抛弃赫图阿拉了。”
长子阿尔通阿侍奉在侧,低声劝道:“阿玛,大伯有他的考虑。沈阳位置重要,便于统御辽东……”
“屁话!”舒尔哈齐激动起来,引发一阵剧烈咳嗽,“他就是不信我!不信这些老兄弟!他要建新都,用新人,把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扔在一边!”
这话说中了痛处。这些年来,努尔哈赤大力提拔新人:蒙古降将、汉人谋士、年轻子侄……像舒尔哈齐这样的开国老臣,反而被冷落。
“阿玛息怒。”次子阿敏(镶蓝旗主)从辽阳赶回探病,“大伯虽然严厉,但对阿玛还是念旧情的。这次迁都,或许是个机会……”
“机会?”舒尔哈齐冷笑,“什么机会?被彻底遗忘的机会?”
“不。”阿敏压低声音,“辽阳的那些汉官、蒙官,反对迁都者甚多。阿玛若能联合老臣,形成一股力量,或许能让大伯改变主意……”
“改变主意?然后呢?继续被边缘化?”舒尔哈齐眼中闪过不甘,“不,阿敏,你不懂。你大伯这个人,一旦做了决定,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跟他硬顶,只有死路一条。”
他喘息片刻,突然抓住阿敏的手:“我死之后,你们要小心。你大伯……不会容你们兄弟掌权的。”
这话说得悲凉,阿敏心中一惊。
果然,一个月后,舒尔哈齐病情加重。临死前,他召集三个儿子(阿尔通阿、阿敏、斋桑古)交待后事:
“记住,不要学我。你大伯是天生的雄主,我们斗不过他。但也要记住,我们是爱新觉罗的子孙,不能任人宰割。要掌兵,要掌权,但……要等时机。”
天命九年(1624年)二月十八,舒尔哈齐病逝于赫图阿拉,享年四十八岁。
消息传到辽阳,努尔哈赤正在批阅迁都的规划图。他放下笔,沉默良久。
“传旨:追封舒尔哈齐为‘庄亲王’,以亲王礼葬。其子阿敏,晋封贝勒,统领镶蓝旗不变。”
旨意简洁,没有过多哀荣。
夜深人静时,努尔哈赤独自站在庭院中,望着北方赫图阿拉的方向。
“二弟,你走在我前面了。”他喃喃自语,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——有悲伤,有愧疚,也有如释重负。
舒尔哈齐的死,消除了一大隐患。但努尔哈赤不知道,这个弟弟临终前的话,将在未来引发更大的风波。
五、沈阳的重建
三月,沈阳的重建工程正式启动。
努尔哈赤任命三贝勒莽古尔泰(第五子)为总监工,抽调三万民夫(多为汉人俘虏和罪犯),日夜赶工。
工程分三部分:
第一,城墙。原沈阳城墙周长九里,努尔哈赤下令扩建到十二里,墙高增至三丈,增设敌楼二十四座。
第二,宫殿。在城中心修建“大政殿”和“十王亭”。大政殿是努尔哈赤理政之处,十王亭则是八旗旗主议事的场所。这种布局,体现了后金“君臣共治”的特色。
第三,城区。将沈阳划分为八区,每区驻一旗,旗民混居。同时修建市场、庙宇、学堂等公共设施。
工程浩大,劳民伤财。
四月,发生了第一起暴动。
三千汉人民夫因不堪劳役,在工地上暴动。他们杀死监工的女真官员,抢夺工具,企图逃跑。
莽古尔泰率兵镇压,当场斩杀五百余人,余者被抓回,处以“车裂”极刑。
消息传到辽阳,范文程紧急求见努尔哈赤。
“大汗,如此严酷,恐激起更大反抗。如今辽东汉人本就心怀怨恨,若再逼迫过甚……”
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努尔哈赤反问,“工程不能停。停了,迁都就成了笑话。”
“可以改变役法。”范文程献策,“将强制劳役改为‘雇役’。汉人民夫每日给工钱,管饭食。同时,允许他们携带家眷,在工地附近安置。”
“钱从哪来?”
“从广宁库银中支取。学生计算过,三万民夫,工期两年,需银约五十万两。而我们缴获的白银,还有两百多万两。”
努尔哈赤沉思。这确实是缓解矛盾的办法,但……给汉人发工钱?女真贵族们会同意吗?
果然,在次日的朝会上,这个提议遭到激烈反对。
“汉人是俘虏、是罪人!给他们干活是天经地义,凭什么发工钱?”
“我们女真人当年建赫图阿拉时,哪个不是自己动手?汉人就这么金贵?”
“范文程这个汉人,处处为汉人说话,其心可诛!”
面对群情激愤,努尔哈赤做了折中:工钱减半,但管饭食;表现优异者,可提前释放,分给土地。
这个方案勉强通过。
事实证明,金钱的力量是巨大的。当汉人民夫得知干活能拿钱、能赎身时,反抗情绪大为缓解。工程进度反而加快了。
到六月,沈阳城墙已修复完毕,大政殿地基打好。努尔哈赤决定:七月正式迁都。
六、迁都盛京
天命九年(1624年)七月初七,辽阳。
这是后金在辽阳的最后一个早晨。城门口,车马辎重排出数里,三万八旗将士、两万家眷、还有无数物资,准备迁往沈阳。
努尔哈赤站在经略府门前,最后看了一眼这座他住了三年的城池。
“大汗,该启程了。”额亦都提醒。
“等等。”努尔哈赤转身,对范文程说,“范先生,你说,我们这一走,辽阳会变成什么样?”
范文程沉吟:“若治理得当,仍是辽东重镇。若治理不当……恐生变乱。”
“你说得对。”努尔哈赤下令,“命何和礼留守辽阳,领正白旗,镇守辽东东部。记住:善待汉民,但也要防着他们。”
“遵旨。”
车驾启程。从辽阳到沈阳一百二十里,走了三天。
七月初十,队伍抵达沈阳。此时沈阳已改名为“盛京”——取“兴盛之都”之意。
新建的城门上,“盛京”两个大字金光闪闪。城墙上,八色旗帜迎风招展。街道两旁,士兵列队迎接。
但努尔哈赤敏锐地察觉到问题:欢迎的人群中,几乎看不到汉人百姓。
“城中汉人都去哪了?”他问莽古尔泰。
“这个……”莽古尔泰支吾,“为了安全,汉人都被迁到城西新区了。”
努尔哈赤脸色一沉:“谁的命令?”
“是……是侄儿自作主张。”莽古尔泰低头,“侄儿觉得,汉人与我们混居,容易生事……”
“糊涂!”努尔哈赤斥责,“满汉分居,看似安全,实则制造隔阂。传令:汉人可以自愿选择居住地,不得强制迁移。”
这个命令,又引起女真贵族的不满。但努尔哈赤坚持:“我们要统治汉地,就要学会与汉人相处。躲着他们,永远成不了大事。”
迁都后的第一次朝会,在大政殿举行。
这是一座八角重檐的建筑,虽然不如明朝宫殿华丽,但气势恢宏。殿前广场上,十座王亭呈八字排列,代表八旗旗主和左右翼统帅。
努尔哈赤坐在大政殿中央的龙椅上,看着台下众臣,心中涌起一股豪情。
从赫图阿拉到界藩,从界藩到辽阳,从辽阳到盛京……这一路走来,他不仅打下了一片疆土,更建立了一个国家的雏形。
但很快,现实的问题接踵而来。
七、稳住蒙古
迁都盛京不到一个月,北方传来急报:蒙古喀尔喀部入侵科尔沁。
科尔沁是后金的盟友,两年前与努尔哈赤联姻(努尔哈赤娶科尔沁贝勒明安之女)。喀尔喀此举,明显是试探后金的反应。
朝会上,主战主和两派争论激烈。
“必须打!科尔沁是我们的屏障,不能丢!”
“可我们现在刚迁都,粮草不足,兵力分散……”
“那就分兵救援!八旗出动四旗,足以击退喀尔喀!”
努尔哈赤一直沉默,直到众人说完,他才开口:“不能打。”
众人愕然。
“不是打不过,是不能打。”努尔哈赤解释,“喀尔喀入侵科尔沁,是试探。我们若大举出兵,正中他们下怀——他们可以边打边退,消耗我们的力量。而我们刚迁都,确实不宜大动干戈。”
“那怎么办?坐视科尔沁被侵?”
“当然不是。”努尔哈赤眼中闪过精光,“派使者去喀尔喀,质问他们为何犯我盟友。同时,集结兵力在边境演习,做出随时出兵的姿态。这叫‘不战而屈人之兵’。”
他顿了顿:“另外,联络蒙古其他部落,特别是与喀尔喀有矛盾的察哈尔部。告诉他们:谁与我为敌,就是与后金为敌;谁与我为友,就是与后金为友。”
这一套组合拳,既展现了强硬,又避免了实际冲突。
果然,喀尔喀见后金反应迅速,且与其他蒙古部落联络,担心被孤立,很快撤兵。
危机暂时解除,但努尔哈赤知道,蒙古问题远未解决。
蒙古诸部就像草原上的狼群,时而联合,时而内斗。要想稳住北方,必须有一套长远的策略。
他召集范文程、额亦都等心腹,制定“蒙古方略”:
一、联姻。继续与蒙古各部通婚,特别是科尔沁、察哈尔等大部。
二、封赏。归顺的蒙古首领,封以爵位,赐予土地。
三、分化。挑拨蒙古各部矛盾,防止他们联合对抗后金。
四、吸纳。招募蒙古勇士加入八旗,充实兵力。
这个方略的核心是:将蒙古从敌人变为盟友,甚至部分吸收进后金体系。
“最难的是第四条。”范文程指出,“蒙古人桀骜不驯,让他们加入八旗,听我们指挥,恐怕不易。”
“那就让他们自成体系。”努尔哈赤早有打算,“设立‘蒙古八旗’,单独编制,由蒙古将领统领,但听我调遣。”
这是一个创举。从此,后金的军事力量由满洲八旗、蒙古八旗、汉军八旗(后来组建)三部分组成。
到天命九年(1624年)底,已有三个蒙古部落归顺,提供骑兵五千。北方边境,暂时稳定。
八、平衡内部
外部刚稳,内部矛盾又起。
迁都盛京后,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。原先在辽阳得势的汉官、蒙官,因为“不熟悉盛京情况”,被边缘化;而女真老臣,则借机夺回权力。
最典型的是五大臣的变动。
原先的五大臣中,额亦都(满)、安费扬古(满)地位稳固;费英东(满)年迈多病,逐渐淡出;何和礼(满)留守辽阳;而扈尔汉(满)因多次顶撞努尔哈赤,被冷落。
新提拔的有:恩格德尔(蒙)、范文程(汉)、达海(满,精通汉文)等。
这种变化,引起了老臣集团的不满。
十月的一次朝会上,扈尔汉当众发难。
“大汗!老臣有话要说!”这位六旬老将须发皆白,但声如洪钟,“我们跟随大汗起兵时,这些汉人、蒙人还在给明朝当狗!现在他们摇身一变,成了我们的‘大人’,对我们指手画脚!老臣不服!”
这话太直接了,殿内一片死寂。
努尔哈赤脸色阴沉:“扈尔汉,你是在质疑我的用人?”
“老臣不敢!”扈尔汉跪地,“老臣只是不明白:我们女真人流血流汗打下的江山,为什么要让外人来坐享其成?”
“外人?”努尔哈赤冷笑,“在你眼里,只有女真人是自己人,汉人、蒙人都是外人?那好,我问你:后金国里,汉人有多少?八十万!蒙古人有多少?二十万!我们女真人有多少?三十万!如果只靠女真人,这江山坐得稳吗?”
他站起身,走下御阶:“打仗时,我们不分满汉蒙,只要杀敌就是勇士。治国时,为什么要分?谁能治国,谁就上!这才是王道!”
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,但能否服众,是另一回事。
当晚,努尔哈赤召见范文程。
“范先生,今日之事,你怎么看?”
范文程苦笑:“大汗,扈尔汉大人代表的是女真老臣的心声。他们担心权力被稀释,担心子孙后代被边缘化。这种担心,不是没有道理。”
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
“平衡。”范文程吐出两个字,“既要重用汉蒙人才,也要安抚女真老臣。比如,可以设立‘议政王大臣会议’,由女真贵族、蒙古贝勒、汉人官员共同组成。大事共议,避免专权。”
“那最终的决策权呢?”
“当然在大汗手中。”范文程说,“但让各方都有发言的机会,他们就会觉得受重视,不满情绪就会减少。”
努尔哈赤采纳了这个建议。
天命十年(1625年)正月,议政王大臣会议正式成立。成员包括:四大贝勒(代善、阿敏、莽古尔泰、皇太极)、五大臣、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、汉官代表范文程等,共十五人。
第一次会议上,讨论的是个敏感话题:是否继续推行剃发令。
蒙古代表明安首先发言:“我们蒙古人留发辫,是天性。强行剃发,恐怕……”
汉官代表范文程谨慎地说:“汉人习俗,确难改变。但既然已推行,若突然停止,恐失威严。”
女真贵族则分成两派:年轻一代认为该继续,彻底汉化;老一代则认为该适当放宽,避免激化矛盾。
争论半天,没有结果。
最终,努尔哈赤拍板:“剃发令继续,但可以做些调整:读书人可以留发髻戴帽遮掩;百姓劳作时可以包头巾。总之,形式上要剃,但实际可以变通。”
这个折中方案,各方勉强接受。
议政会议虽然效率不高,但确实起到了平衡各方、缓解矛盾的作用。后金的统治,在磕磕绊绊中向前推进。
九、朝鲜的试探
内部刚稳,东方又起波澜。
朝鲜光海君虽然在三年前萨尔浒之战后与后金修好,但内心始终视后金为“蛮夷”,暗地里仍与明朝联络。
天命十年(1625年)三月,朝鲜发生政变:光海君被废,其侄绫阳君李傧即位,是为仁祖。新王即位后,立即调整国策:疏远后金,亲近明朝。
四月,朝鲜使者来到盛京,递交国书。国书中语气倨傲,称努尔哈赤为“建州酋长”,要求后金归还萨尔浒之战时俘虏的朝鲜将士。
“放肆!”莽古尔泰大怒,“一个小小的朝鲜,也敢对我们指手画脚!”
努尔哈赤却很冷静。他看完国书,问使者:“这是你们大王的意思,还是朝中大臣的意思?”
使者昂首:“自然是大王的意思。”
“好。”努尔哈赤点点头,“回去告诉你家大王:俘虏的朝鲜将士,愿意归顺的已编入我军,不愿归顺的早已放回。至于称呼……我努尔哈赤是后金大汗,不是什么酋长。若你家大王不懂礼数,我可以教他。”
这话绵里藏针,使者脸色一变。
使者走后,众臣议论纷纷。
“朝鲜反复无常,该打!”
“可我们现在兵力不足,同时对付明朝和朝鲜,恐怕……”
努尔哈赤早有打算:“朝鲜是要打的,但不是现在。我们现在的主要敌人是明朝。朝鲜……可以先敲打敲打。”
他做了三件事:
第一,派兵在鸭绿江边演习,做出要渡江的姿态。
第二,断绝与朝鲜的贸易,特别是粮食和铁器贸易。
第三,支持朝鲜国内的亲后金势力,暗中给光海君残余势力提供援助。
这三招组合,效果显著。
朝鲜仁祖刚即位,国内不稳。听说后金在边境集结兵力,大惊失色,急忙派第二波使者来解释:前次国书是“误用旧式”,绝非有意冒犯。
同时,朝鲜国内粮价飞涨,铁器短缺,民生困苦。
到六月,朝鲜不得不低头:重新递交国书,称努尔哈赤为“大汗”,恢复贸易,并承诺“不与明朝联合攻金”。
朝鲜问题,暂时解决。
但努尔哈赤知道,这只是权宜之计。朝鲜这个国家,畏威而不怀德。只有彻底打败它,才能真正收服。
可现在,还不是时候。
十、八旗贵族的密谋
就在努尔哈赤忙于应对内外挑战时,盛京城内,一场密谋正在酝酿。
参与者是几个对现状不满的八旗贵族:镶红旗主杜度(褚英长子,努尔哈赤长孙)、正蓝旗主德格类(莽古尔泰之弟)、镶白旗主阿济格(努尔哈赤第十二子)等。
他们在阿济格府邸的地下密室聚会,烛光昏暗,气氛诡秘。
“大汗越来越偏信汉人了。”杜度首先开口,“范文程那个奴才,现在竟然可以参与议政会议!我们这些爱新觉罗的子孙,反而要听他指手画脚!”
“还有那些蒙古人。”德格类补充,“恩格德尔有什么功劳?不就是会拍马屁吗?现在居然成了户部承政,管着我们的钱粮!”
阿济格年纪最小(十九岁),但野心最大:“要我说,大汗老了,糊涂了。该换人了。”
这话太大胆,众人都是一惊。
“换谁?”杜度问,“四大贝勒中,代善软弱,阿敏是舒尔哈齐之子,莽古尔泰有勇无谋,皇太极……倒是个人物,但他会听我们的吗?”
“所以不能明着来。”阿济格眼中闪过阴狠,“我们可以……让大汗‘自然’退位。”
“你是说……”
“下毒。”阿济格压低声音,“我认识一个朝鲜医生,擅长用慢性毒药。神不知鬼不觉,三个月见效。到时候大汗‘病逝’,我们拥立一个听话的……”
“住口!”杜度厉声打断,“你这是谋逆!被发现了,是要灭族的!”
“那你说怎么办?”阿济格不服,“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权力落到外人手里?”
德格类打圆场:“阿济格也是为我们女真人着想。不过下毒太冒险了。不如这样:我们联合起来,在议政会议上施压,要求限制汉蒙官员的权力。大汗再强势,也不能不顾我们这些旗主的意见。”
这个建议相对稳妥,众人同意。
但他们不知道,这场密会刚结束,消息就传到了努尔哈赤耳中。
报告者是皇太极——这位四贝勒虽然年轻(三十三岁),但心思缜密,在八旗中安插了不少眼线。
“父汗,阿济格他们……”皇太极欲言又止。
努尔哈赤摆手:“我知道了。年轻人,有想法是正常的。只要不越线,就随他们去。”
“可是他们若真在议政会议上发难……”
“那就让他们发。”努尔哈赤冷笑,“我倒要看看,他们能掀起多大浪。”
果然,在下次议政会议上,杜度等人发难了。
他们提出“八旗事务应由旗主自主,汉蒙官员不得干涉”,还要求“重要官职必须由女真人担任”。
这等于要剥夺汉蒙官员的实权。
会议上吵成一团。女真贵族大多支持,汉蒙官员强烈反对。
努尔哈赤一直冷眼旁观,直到吵得不可开交时,才开口:
“都说完了?”他声音平静,但透着威严,“那我来说两句。”
全场安静。
“八旗是我亲手所创,旗主是我亲自任命。你们要自主?可以。把旗主之位交出来,我换人。”
众人色变。
“至于汉蒙官员……他们能坐在这里,是因为有能力。你们谁不服,可以比一比:比治国,比打仗,比什么都行。赢了的,我重用。输了的,闭嘴。”
这话堵死了所有人的嘴。比治国?这些女真贵族大多是武夫,哪里比得过范文程这样的文人?比打仗?汉蒙官员中也有能征善战者。
“还有问题吗?”努尔哈赤扫视众人。
无人敢应。
“散会。”
这次风波,以努尔哈赤的绝对权威告终。但也暴露了深层次矛盾:新生代贵族对现状不满,渴望更多权力。
努尔哈赤意识到,必须未雨绸缪。
十一、确立继承制度
天命十年(1625年)八月,盛京。
六十七岁的努尔哈赤感到身体大不如前。征战多年的旧伤在阴雨天隐隐作痛,批阅奏章时眼睛也开始模糊。
他知道,该考虑身后事了。
继承问题,是每个王朝最棘手的问题。女真传统是“幼子守灶”(幼子继承家业),但国家不是家业,不能简单套用。
他有十六个儿子,其中有能力者不少:次子代善(四十三岁),为人宽厚,在八旗中威望高;五子莽古尔泰(三十八岁),勇猛善战,但性格暴躁;八子皇太极(三十三岁),文武双全,心思深沉;还有十四子多尔衮(十三岁),虽然年幼,但聪慧过人……
该选谁?
他首先排除了多尔衮——太年轻,压不住那些老臣。也排除了莽古尔泰——有勇无谋,非治国之才。
剩下代善和皇太极。
代善的优势是年长、稳重、人缘好。缺点是过于宽厚,缺乏决断力。
皇太极的优势是能力强、有手段、得人心(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)。缺点是……太有能力了,让努尔哈赤隐隐不安。
九月,努尔哈赤做了一次试探。
他召集四大贝勒(代善、阿敏、莽古尔泰、皇太极)和五大臣,宣布:“我年纪大了,精力不济。从今天起,国家大事由四大贝勒共议决定,五大臣辅佐。遇事不决,再报我。”
这是放权,也是考验。
他想看看,在权力面前,这些儿子们会如何表现。
结果不出所料。
代善事事谦让,不敢做主;莽古尔泰独断专行,听不进意见;阿敏(舒尔哈齐之子)则处处与皇太极作对;只有皇太极,既能提出建设性意见,又能协调各方矛盾。
一个月下来,皇太极的实际影响力已超过其他三人。
努尔哈赤心中有数了。
十月,他单独召见皇太极。
“老八,这一个月,你觉得四大贝勒共议,效果如何?”
皇太极谨慎回答:“众人同心,自然好。但若各怀心思,反而误事。”
“那你说,该怎么解决?”
“儿臣以为,共议可以,但必须有最终决断之人。否则一事无成。”
努尔哈赤盯着儿子:“那你觉得,谁该是这个决断之人?”
皇太极跪下:“此等大事,唯有父汗圣裁。”
答得滴水不漏。
努尔哈赤笑了:“起来吧。我知道你的能力,也知道你的心思。但你要记住:治国不仅靠能力,还要靠德行。要团结兄弟,善待臣民,不能只想着权力。”
“儿臣谨记。”
这次谈话后,努尔哈赤虽然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,但已经倾向皇太极。
他做了几项安排:
第一,提升皇太极在议政会议中的地位,让他负责吏部和兵部。
第二,将两黄旗(最精锐的部队)交由皇太极实际掌管。
第三,让皇太极主持编纂《太祖实录》,这等于承认他的“文治”能力。
这些安排,明眼人都看得出来:皇太极是实际上的储君。
但努尔哈赤留了一手:没有正式下诏。他在等,等一个更合适的时机,也等皇太极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位置。
十二、盛京的冬天
天命十年(1625年)冬,盛京下了第一场雪。
雪花纷飞中,努尔哈赤站在大政殿前,望着这座他亲手重建的都城。
三年了。从迁都辽阳,到再迁盛京,这三年里,他稳住了蒙古,震慑了朝鲜,平衡了内部,确立了继承制度。
后金这个新生政权,在风雨飘摇中站稳了脚跟。
但前路依然艰难。
南方,明朝正在孙承宗、袁崇焕等人的主持下,整军备战。宁远、锦州一线,明军修筑了坚固的防线。
西方,蒙古察哈尔部虽然暂时臣服,但随时可能反复。
内部,满汉矛盾、新旧矛盾、兄弟矛盾,依然存在。
六十七岁的努尔哈赤,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。
“父汗。”皇太极不知何时来到身后,为他披上大氅,“天冷了,回宫吧。”
努尔哈赤没有动:“老八,你说,我们还能走多远?”
皇太极沉默片刻:“儿臣不知道能走多远,但知道必须往前走。停下来,就是死路。”
“说得好。”努尔哈赤转头看着儿子,“我这一生,从十三副甲起兵,到今天坐拥辽东,靠的就是不断往前走。你记住了:做君王,不能回头,只能向前。”
“儿臣记住了。”
雪花落在努尔哈赤的肩头,渐渐积了一层。这个老人,这个君王,这个时代的开创者,在盛京的雪夜中,思考着未来。
他知道,自己时日无多了。但后金的路,还很长。
“明年开春,”他突然说,“我要亲征宁远。”
皇太极大惊:“父汗!宁远城防坚固,袁崇焕不是易与之辈。而且父汗年事已高……”
“正因为年事已高,才要打这一仗。”努尔哈赤眼中燃烧着最后的光芒,“我要在死前,为你们扫清最大的障碍。宁远不下,山海关难破;山海关不破,北京难图。”
这是最后的豪赌。
赢了,后金将打开通往华北的大门。
输了……努尔哈赤不敢想。
但他必须赌。
因为他是努尔哈赤,是后金的开国之君。他的使命,就是为子孙后代铺平道路。
哪怕这条路,要用自己的鲜血来铺。
雪越下越大,覆盖了盛京的宫殿,覆盖了街道,也覆盖了远方的战场。
但覆盖不了这个老人心中的火焰。
那火焰,燃烧了四十四年,从十三副甲起兵那天起,就从未熄灭。
现在,它要燃烧最后一次。
为了后金,为了女真,也为了他未竟的梦想。
发表评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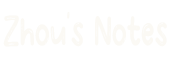





暂时没有评论,来抢沙发吧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