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皇太极)第九章:失爱妃摧心肝,胜松锦收良将
一、白幡蔽宫,帝王崩泪
崇德六年(1641年)八月,盛京皇宫素白一片。
海兰珠的灵柩停放在关雎宫正殿,殿内白幡低垂,香烟缭绕。皇太极已在此守灵三日,不吃不喝,不眠不休,只是怔怔地望着那口楠木棺椁,仿佛下一刻,那个温柔的女子就会推开棺盖,笑着对他说“陛下,臣妾吓着您了”。
但棺椁始终沉寂。
哲哲皇后第三次端着食盘进来,轻声劝道:“陛下,多少用些吧。宸妃妹妹在天有灵,也不愿见陛下如此。”
皇太极恍若未闻,手指轻轻抚过棺木上雕刻的凤凰纹路。那是他亲自设计的图案,凤凰于飞,和鸣锵锵——他曾说,海兰珠就是他的凤凰,如今凤凰折翼,留他独对九天。
“她走的时候,说什么了吗?”他忽然开口,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。
哲哲眼圈一红:“妹妹最后说……‘告诉陛下,臣妾不悔’。”
“不悔……”皇太极重复这两个字,忽然惨笑,“她当然不悔。悔的是朕!朕不该让她怀孕,不该让她随军,不该……不该活着回来!”
最后一句几乎是嘶吼出来的。他猛地站起,却又因三日水米未进而踉跄跌倒,额头重重磕在棺椁上,鲜血顺着眉骨流下。
“陛下!”哲哲惊呼,忙上前搀扶。
皇太极推开她,手扶棺木,缓缓站直。鲜血混着泪水,在他脸上划出触目惊心的痕迹。
“你们都出去。”他低声说,“让朕……一个人陪陪她。”
哲哲欲言又止,最终叹了口气,领着宫人退下。殿门关闭的刹那,她回头看了一眼——那个曾叱咤风云、令明朝闻风丧胆的大清皇帝,此刻佝偻着背,额头抵着妻子的棺木,肩膀微微颤抖,像个失去一切的孩子。
殿内彻底安静下来。香烛燃烧的噼啪声,成了唯一的声响。
皇太极慢慢滑坐在棺椁旁,背靠着冰冷的楠木。他想起第一次见海兰珠的情景,那是天聪八年,在科尔沁的草原上。她穿着蒙古袍子,在马上回眸一笑,眼睛亮得像草原上的星星。他当时就想,这个女子,他要定了。
后来她入宫,不争不抢,只是安静地陪在他身边。他批阅奏折到深夜,她就默默在一旁做针线;他因朝政烦心,她就弹一曲蒙古长调;他出征在外,她的书信总是那句“臣妾安好,陛下勿念”。
“你说你安好……”皇太极喃喃自语,手指在棺木上划着,“可朕回来了,你却走了。海兰珠,你骗朕。”
他想起她怀孕时的喜悦,想起她抚摸肚子时温柔的眼神,想起她说“等孩子出生,陛下教他骑马射箭,臣妾教他读书写字”。那时他们多幸福啊,仿佛天下都是他们的。
可现在,孩子生了,她却没了。福临在乳母怀里嗷嗷待哺,却永远见不到母亲的模样。
“朕答应过你,要带你去江南,泛舟西湖,听雨秦淮。”皇太极的声音哽咽了,“朕……朕食言了。”
殿外忽然传来喧哗声。皇太极皱眉,正要呵斥,殿门被推开,豪格大步闯了进来。
“父汗!”豪格一身戎装,风尘仆仆,显然是刚从松锦前线赶回,“儿臣听说……”
“谁让你进来的?”皇太极冷冷打断他,“出去。”
豪格一愣,看见父亲满脸血泪的惨状,心中震撼,但还是硬着头皮说:“父汗,儿臣有要事禀报。洪承畴已押至盛京,如何处置,请父汗定夺。还有松锦诸城防务,各旗将士封赏……”
“出去。”皇太极的声音提高,“朕说,出去。”
“可是父汗,国事为重啊!宸妃娘娘已逝,您再悲伤她也回不来了。可大清……”
“滚!”
皇太极抓起手边的香炉,狠狠砸了过去。铜制香炉擦着豪格的耳边飞过,砸在门框上,香灰洒了一地。
豪格脸色煞白,跪地:“父汗息怒!儿臣……儿臣只是……”
“只是什么?只是觉得朕不该为一个女人如此?”皇太极站起身,一步步走向豪格,眼神冰冷如刀,“豪格,你记住:海兰珠不仅是朕的妃子,还是你弟弟的母亲,是大清的宸妃!她的生死,就是国事!”
他俯视着跪在地上的长子:“你现在,立刻,滚出去。没有朕的旨意,不准再踏入关雎宫一步。”
“父汗……”
“滚!”
豪格咬了咬牙,终究不敢违逆,低头退出。殿门重新关闭。
皇太极踉跄着走回棺椁旁,颓然坐下。豪格说得对,国事为重,他不能一直沉浸在悲痛中。可是……心真的好痛,痛得像被人剜去了一块。
“海兰珠,你告诉朕,朕该怎么办?”他闭上眼,泪水无声滑落。
殿外,哲哲拦住一脸愤懑的豪格。
“大阿哥,你太急了。”她叹息,“陛下现在正伤心,你该体谅。”
豪格冷哼:“皇后娘娘,儿臣是为大清着急!松锦大捷,洪承畴被擒,正是乘胜追击、直取山海关的好时机!可父汗却……却为了个女人,连朝都不上了!这要是传出去,军心怎么办?民心怎么办?”
“放肆!”哲哲厉声,“宸妃也是你能妄议的?”
豪格自知失言,低头:“儿臣知错。但请皇后娘娘劝劝父汗,国事真的耽误不得了。”
哲哲看着这个鲁莽的侄子,心中复杂。豪格勇猛善战,但缺了那份帝王应有的深沉和隐忍。若皇太极真有个万一,他镇得住这朝堂吗?
“本宫会劝的,你先去处理洪承畴之事,好生看管,莫要怠慢。”
“是。”
豪格退下后,哲哲望向紧闭的殿门,长长叹了口气。她想起海兰珠临终前拉着她的手说:“姐姐,陛下就拜托您了。”
“妹妹放心。”她当时这样答应。可现在,她要如何履行这个承诺?
这时,庄妃布木布泰悄无声息地走了过来。她是哲哲的亲侄女,今年二十七岁,聪慧沉稳,在后宫中仅次于皇后和已故的宸妃。
“姑母,陛下还是不肯出来吗?”
哲哲摇头:“三日了,水米未进。再这样下去,龙体怎么撑得住?”
布木布泰沉吟片刻:“或许……可以让福临试试。”
“福临?”
“陛下虽悲痛,但舐犊之情难断。福临是宸妃姐姐留下的唯一骨血,陛下见了,或许能稍解悲痛。”
哲哲眼睛一亮:“你说得对。去,让乳母把八阿哥抱来。”
片刻后,乳母抱着襁褓中的福临来了。孩子刚满月,小脸皱巴巴的,正熟睡着。
哲哲接过孩子,轻轻推开殿门。皇太极仍坐在棺椁旁,听见动静,头也不回:“朕说了,谁都不准进来。”
“陛下,是福临。”哲哲轻声道,“孩子饿了,哭着想找父皇。”
皇太极身体一僵,缓缓回头。当看见哲哲怀中那个小小的襁褓时,他的眼神瞬间柔软下来。
“给朕。”他伸出手。
哲哲将福临递过去。皇太极笨拙地抱着孩子,动作小心翼翼,生怕碰坏了这脆弱的小生命。福临被惊醒了,睁着乌溜溜的眼睛,看着眼前这个满脸血泪的男人,忽然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
“不哭,不哭。”皇太极手足无措地哄着,声音是从未有过的温柔,“父皇在这儿,父皇在这儿。”
说来也怪,福临哭了几声,竟慢慢止住了,还伸出小手,抓住了皇太极的一根手指。
那一瞬间,皇太极的眼泪夺眶而出。他抱着孩子,跪在妻子的棺椁前:“海兰珠,你看见了吗?这是咱们的福临,他抓住朕的手指了……他长得像你,眼睛像,鼻子也像……”
哲哲悄悄退出,关上门。她知道,这一刻,属于他们一家三口。
殿内,皇太极抱着儿子,对着妻子的棺椁,说了很久很久的话。说他第一次抱孩子时的紧张,说福临吃奶时的模样,说他将来要如何教育这个孩子……
说着说着,他忽然道:“海兰珠,你放心,朕会振作起来的。为了你,为了福临,为了大清,朕不能倒下。”
他擦干眼泪,轻轻将福临放在棺椁旁的软垫上,然后站起身,整理衣冠。虽然依旧憔悴,但眼中已重新有了神采。
“来人。”他朝殿外唤道。
哲哲推门进来:“陛下。”
“传旨:宸妃海兰珠,温惠性成,柔嘉维则,侍朕多年,克尽敬慎。今追封为敏惠恭和元妃,以皇后礼葬于昭陵之侧。举国守孝三日,辍朝七日。”
“是。”哲哲顿了顿,“那朝政……”
“明日复朝。”皇太极看着棺椁,轻声道,“她不会愿意看到朕因为她而荒废朝政的。”
他又抱起福临,在孩子额头轻轻一吻:“福临,父皇要去打天下了。等你长大,父皇给你一个太平盛世。”
福临似乎听懂了,咧开没牙的嘴,笑了。
那一刻,皇太极知道,他必须活下去,必须坚强。因为他不仅是海兰珠的丈夫,更是福临的父亲,是大清的皇帝。
悲伤可以藏在心底,但责任必须扛在肩上。
这是帝王的路,注定孤独,但必须走下去。
二、洪承畴绝食,庄妃劝降
洪承畴被关押在盛京城南的驿馆中,已绝食五日。
这位五十三岁的明朝蓟辽总督,虽成阶下囚,但脊梁挺得笔直。他坐在简陋的木床上,闭目养神,对桌上每日更换的珍馐美味看都不看一眼。
看守的侍卫私下议论:“这洪老头还真硬气,五天不吃不喝,居然还撑得住。”
“听说皇上下令,必须好生伺候,不能让他死了。”
“那是,皇上想收服他呢。松锦之战,就他最难打,皇上敬他是条汉子。”
正说着,驿馆外传来马蹄声。侍卫连忙列队迎接——来的是庄妃布木布泰。
这位妃子今日穿着素色宫装,只戴一支玉簪,朴素得不像个妃嫔。她带着两个侍女,提着一个食盒,缓步走进驿馆。
“洪大人可好?”她问侍卫。
“回娘娘,还是老样子,不吃不喝。”
布木布泰点头:“开门,本宫去看看。”
房门打开,洪承畴睁开眼,看见一个年轻女子进来,微微皱眉:“你是何人?”
“大清庄妃,博尔济吉特氏。”布木布泰微微欠身,“奉皇上之命,特来探望洪大人。”
洪承畴冷笑:“皇太极要劝降,派个女人来?未免太小瞧洪某了。”
“洪大人误会了。”布木布泰不恼,让侍女摆开食盒,里面是几样清粥小菜,“皇上知大人绝食,心中敬佩,特命御膳房做了些江南口味的小菜。皇上说,大人是福建人,想必想念家乡味道了。”
这话让洪承畴一愣。他是福建南安人,离家二十余年,确实时常想念家乡的粥菜。眼前这几样:蚵仔煎、面线糊、花生汤,都是地道闽南小吃。
“皇上连这个都知道?”他声音有些发涩。
“皇上常说,要用人,先要知人。”布木布泰盛了一碗面线糊,递过去,“洪大人,蝼蚁尚且贪生,何况人乎?您为大明朝尽忠职守,力战被擒,已对得起崇祯皇帝了。如今绝食求死,除了成全自己的名节,于国于民又有何益?”
洪承畴不接,反问:“庄妃娘娘是蒙古人吧?为何要为满洲人说话?”
“因为大清不是满洲人的大清,是天下人的大清。”布木布泰正色道,“皇上设立六部,重用汉臣,开科取士,满汉一体。洪大人熟读史书,当知历朝历代,能如此包容者有几?”
她顿了顿,继续道:“反观明朝,崇祯皇帝多疑寡恩,朝中党争不断,百姓流离失所。洪大人镇守辽东多年,朝廷给的粮饷可足?援兵可及时?朝中可有人为大人说话?”
这话句句戳中洪承畴痛处。松锦之战,他十三万大军粮草不继,朝廷催战却不给补给,援军迟迟不到。若非如此,何至于一败涂地?
“那是朝中奸臣误国,非皇上之过。”他咬牙道。
“真的是奸臣误国吗?”布木布泰轻叹,“崇祯皇帝登基十七年,换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,杀了七个总督,十一个巡抚。洪大人,您觉得下一个会是谁?”
洪承畴沉默了。他想起袁崇焕,那个被凌迟处死的一代名将;想起孙传庭,那个战死沙场却还要被追责的陕西总督。崇祯皇帝刻薄寡恩,是朝野共识。
“洪大人,”布木布泰将碗又往前递了递,“大清皇上求贤若渴,对范文程、宁完我等汉臣礼遇有加。祖大寿两度降清,皇上仍以总兵相待。皇上说,洪大人若肯归顺,必以国士待之,共谋天下太平。”
洪承畴看着那碗面线糊,热气腾腾,香味扑鼻。他已经五天没吃东西了,腹中饥饿难耐。更重要的是,布木布泰的话,句句在理。
死,容易;活着,难。但活着,或许真能做些什么。
“庄妃娘娘,”他终于开口,“洪某有一个问题。”
“请讲。”
“若洪某归顺,皇上要洪某做什么?去打明朝?去杀旧日同僚?”
布木布泰摇头:“皇上说,洪大人只需做三件事:第一,养好身体;第二,将辽东治理经验写成书,传于后世;第三,若将来入主中原,帮皇上安抚百姓,整顿吏治。”
她看着洪承畴:“皇上还说,洪大人是儒将,当知‘民为重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’。如今明朝气数已尽,李自成破河南,张献忠陷湖广,百姓水深火热。洪大人是要为一家一姓尽忠,还是为天下苍生谋福?”
这句话,成了压垮洪承畴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他想起辽东战死的将士,想起饿死在锦州的百姓,想起中原流离失所的难民。是啊,他读圣贤书,学的是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”。可这些年,他到底在为谁而战?
“罢了……”洪承畴长叹一声,接过那碗面线糊,“洪某……愿降。”
布木布泰眼中闪过喜色,但面上仍保持平静:“洪大人明智。皇上已在宫中设宴,请大人沐浴更衣后,随本宫入宫。”
当洪承畴梳洗完毕,换上干净衣袍,随布木布泰走进大清皇宫时,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
不是震撼于宫殿的宏伟——他见过北京的紫禁城,盛京皇宫远不能比。他震撼的是,沿途所见官员,满汉皆有,各司其职;宫中礼仪,井然有序,不输明朝;甚至看到几个蒙古王公与汉官谈笑风生,毫无隔阂。
“洪大人觉得如何?”布木布泰问。
“颇有……新朝气象。”洪承畴由衷道。
“这才只是开始。”布木布泰微笑,“皇上说,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超越元明的大帝国。洪大人,您赶上了好时候。”
来到崇政殿,皇太极已在等候。他今日穿着常服,神色虽仍憔悴,但已恢复了帝王的威仪。
“罪臣洪承畴,拜见皇上。”洪承畴跪地。
皇太极亲自扶起他:“洪先生快快请起。从今日起,你我不是君臣,是朋友,是同志。来,坐。”
他拉着洪承畴坐下,指着殿中悬挂的地图:“洪先生请看,这是朕画的大清疆域图。辽东已定,蒙古臣服,朝鲜归顺。下一步,就是这里——”他的手指点在山海关,“入主中原,一统天下。”
洪承畴看着地图,心中澎湃。他在明朝为官三十年,从未见过皇帝如此坦诚,如此有抱负。崇祯皇帝除了催战、催饷、问责,何曾与他畅谈过天下大势?
“皇上志向远大,罪臣佩服。只是……入关之路,恐非易事。”
“所以需要先生相助。”皇太极诚恳地说,“先生熟谙中原情况,又知兵善战。朕欲拜先生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,参赞军机。待时机成熟,随朕入关,安抚百姓,整顿河山。”
洪承畴再次跪倒:“皇上如此信任,臣……必竭尽全力,以报知遇之恩!”
“好!好!”皇太极大喜,亲自斟酒,“来,朕与先生满饮此杯,共谋大业!”
两人对饮,相谈甚欢。从辽东防务,到中原民情,从用兵之道,到治国之策,洪承畴发现,这位满洲皇帝对汉文化的了解,对天下大势的把握,远在许多明朝官员之上。
宴席至半,皇太极忽然问:“先生可知,朕为何能取得松锦大捷?”
洪承畴沉吟:“皇上用兵如神,臣自愧不如。”
“不。”皇太极摇头,“朕能胜,是因为上下一心。八旗将士听朕号令,满汉官员各司其职。而明朝败,败在内耗。君疑臣,臣疑将,将疑兵。一盘散沙,如何能战?”
他顿了顿,眼中闪过痛色:“就像朕的宸妃去世,朕悲痛欲绝,但朝中诸臣各尽其责,未生乱象。若在明朝,皇帝三日不朝,只怕早已流言四起,党争不休了。”
洪承畴深以为然。他在明朝为官,深受党争之苦。东林党、阉党、浙党、楚党……彼此攻讦,不顾国事。松锦之战时,朝中还有人弹劾他“养寇自重”,真是可笑又可悲。
“皇上圣明。”他由衷道,“臣在明朝三十年,未见如此清明之政。”
“清明还谈不上。”皇太极叹道,“朕也有朕的难处。满汉之隔,新旧之争,立储之事……每一件都让朕头疼。”
他看向洪承畴:“所以朕需要先生这样的能臣,帮朕化解矛盾,凝聚人心。大清要走的,是一条前所未有的路。朕希望,先生能与朕同行。”
洪承畴心中涌起一股久违的豪情。五十多岁了,本已心灰意冷,准备绝食殉国。没想到峰回路转,遇到这样一位明主,还能参与开创一个新时代。
“臣……愿随皇上,赴汤蹈火,在所不辞!”
那一夜,崇政殿的灯火亮到很晚。一个满洲皇帝,一个汉人降臣,对着地图,规划着天下的未来。
而在殿外,布木布泰静静站着,听着里面的谈话声,嘴角露出微笑。她完成了皇太极交给她的任务,也为大清赢得了一位良将。
更重要的是,她让皇太极看到了她的能力。
“姑母说得对。”她轻声自语,“后宫女子,未必不能参与前朝之事。关键是要找对方法,用对时机。”
她望向关雎宫的方向,那里还挂着白幡。海兰珠死了,但后宫不会永远空着那个位置。谁能填补那个空缺,不仅要看皇上的心意,还要看自己的本事。
而她布木布泰,有这个本事。
三、多尔衮献玺,暗流再生
九月,多尔衮从蒙古班师回朝。
这次西征,他不仅彻底剿灭了林丹汗残部,还在鄂尔多斯草原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收获——一方传国玉玺。
玉玺被恭恭敬敬地呈到崇政殿。皇太极看着这方四寸见方、螭龙钮、刻着“制诰之宝”的玉玺,神色复杂。
“十四弟又立大功了。”他缓缓道,“此玺乃是元朝遗物,象征天命。今日得之,实乃天佑大清。”
多尔衮跪地:“此乃皇上洪福齐天,臣弟不过恰逢其会。”
“恰逢其会?”皇太极笑了笑,“恐怕不是吧。朕听说,为了这方玉玺,你屠了额哲(林丹汗之子)全家?”
多尔衮心中一凛,面上却不动声色:“额哲冥顽不灵,拒不归顺,臣弟不得已而为之。”
“不得已……”皇太极抚摸着玉玺,“十四弟,你今年二十五了吧?年轻有为,战功赫赫,如今又献上玉玺,朕该如何赏你呢?”
这话意味深长。多尔衮连忙叩首:“臣弟不敢求赏。为皇上分忧,为大清效力,是臣弟的本分。”
“本分……”皇太极重复这个词,忽然问,“十四弟,你觉得朕对你如何?”
“皇上对臣弟恩重如山!”多尔衮诚惶诚恐,“若非皇上提拔,臣弟何能有今日?”
“那朕若让你交出兵权,回盛京享福,你可愿意?”
空气瞬间凝固。殿中侍立的太监、侍卫都低下头,不敢出声。多尔衮跪在地上,手心里全是汗。
良久,他抬起头,眼中含泪:“皇上若觉得臣弟碍眼,臣弟愿交出兵权,做个闲散亲王。只是……只是臣弟还想为皇上效力,还想看着大清入主中原。”
这话说得情真意切,连皇太极都有些动容。他亲自扶起多尔衮:“十四弟说哪里话?朕怎会疑你?只是你常年征战,太过辛苦,朕心疼你。”
他顿了顿:“这样吧,你刚回来,先歇几个月。正白旗、镶白旗的事务,暂时交给多铎打理。等养好了精神,朕还有重任交给你。”
“臣弟……遵旨。”多尔衮低头,眼中闪过一丝阴霾。
这是明升暗降。名义上是让他休息,实则是夺了他的兵权。多铎是他亲弟弟,但年轻气盛,缺乏谋略,两白旗交给他,等于削弱了多尔衮的势力。
“去吧,好好休息。”皇太极拍拍他的肩,“你福晋乌兰刚生了儿子,多陪陪他们。”
“谢皇上关怀。”
多尔衮退出崇政殿,走出宫门时,脸色已阴沉如水。亲信何洛会迎上来,见他神色不对,低声问:“王爷,皇上……”
“回府再说。”
回到睿亲王府,多尔衮屏退左右,只留何洛会一人。
“皇上要夺我的兵权。”他冷冷道,“让我‘休息’,两白旗交给多铎。”
何洛会大惊:“这……这是为何?王爷刚立大功啊!”
“功高震主,你不懂吗?”多尔衮冷笑,“皇太极现在越来越像汉人皇帝了,猜忌多疑。我献玉玺,他不但不喜,反而觉得我在邀功,在收买人心。”
他走到窗前,望着皇宫的方向:“还有洪承畴,那个汉人降将,现在成了皇太极的座上宾。范文程、宁完我这些汉臣,一个个位高权重。而我们这些满人亲王,反而被边缘化。”
“王爷,那我们……”
“等。”多尔衮眼中闪过寒光,“皇太极身体越来越差了,我看得出来。海兰珠的死,对他打击太大。只要他有个万一……”
他没有说下去,但何洛会明白了。皇太极若去世,继位的是谁?豪格?福临?还是其他皇子?无论谁继位,都需要辅政大臣。而多尔衮,有这个资格。
“王爷英明。”何洛会低声道,“那我们……”
“继续韬光养晦。”多尔衮道,“告诉下面的人,这段时间都安分些。尤其是我那个弟弟多铎,别让他惹事。两白旗虽然交给他,但实际控制权,还得在我手里。”
“是。”
“还有,”多尔衮想起什么,“乌兰那边,让她多进宫,跟庄妃走动走动。布木布泰这个女人不简单,她劝降洪承畴的事,我听说了。这样的女人,值得结交。”
“属下明白。”
何洛会退下后,多尔衮独自坐在书房中。他想起母亲阿巴亥,想起她殉葬那天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十五岁,跪在陵墓外,听着母亲的哭喊声渐渐微弱,心中充满了仇恨。
这么多年了,他忍辱负重,一步步爬上权力高峰。可皇太极还是防着他,像防贼一样。
“皇太极,你给我的,我会记住。”他喃喃自语,“你不给我的,我也会自己拿。”
而在皇宫中,皇太极也在与范文程谈论多尔衮。
“先生觉得,朕对多尔衮是否太苛了?”
范文程沉吟道:“皇上用心良苦。睿亲王年轻有为,但锋芒太露,易招人妒。让他歇一歇,既是保护他,也是磨砺他。”
“你看出来了?”皇太极苦笑,“朕确实在保护他。豪格对他不满已久,朝中也有大臣弹劾他‘专权跋扈’。若再让他掌兵,恐生事端。”
他顿了顿:“但朕也在防他。多尔衮有才干,有野心,若不加约束,将来必成祸患。朕在时,还能压得住他。朕若不在了……”
他没有说下去,但范文程明白。皇帝这是在考虑身后事。
“皇上,立储之事……”范文程试探道。
皇太极沉默良久:“豪格勇猛,但缺谋略;福临年幼,尚不知贤愚;其他皇子,或平庸,或年幼。朕……难以决断。”
“那皇上可曾想过,效仿先汗旧制,由诸王贝勒共推?”
“共推?”皇太极摇头,“那是部落时代的做法。如今大清已是帝国,要有章法,有制度。朕这些年设六部,定官制,就是为了摆脱部落旧习。若立储之事再回到老路,前功尽弃。”
他站起身,走到地图前:“所以朕要活久一些,至少要看到福临长大,看到他是不是可造之材。”
范文程心中叹息。皇帝才五十二岁,但海兰珠去世后,他明显苍老了许多,身体也大不如前。要等到福临成年,至少还要十五年。皇上撑得到吗?
“皇上要保重龙体。”他只能这样说。
“朕知道。”皇太极望着窗外,“为了大清,朕会好好活着。”
话虽如此,当夜他还是失眠了。一个人躺在清宁宫的龙床上,身边空荡荡的。以前海兰珠在时,总会为他揉肩捶背,陪他说话。现在,只有冰冷的被褥。
他起身,走到偏殿。福临睡在乳母身边,小脸恬静。皇太极轻轻抱起儿子,走到窗前。
“福临,你娘不在了,以后就咱们爷俩相依为命了。”他低声说,“父皇会为你铺好路,让你将来能坐稳这个江山。”
福临在睡梦中咂了咂嘴,小手无意识地抓住了皇太极的衣襟。
那一刻,皇太极下定了决心。无论多难,他都要为这个孩子扫清障碍,包括那些可能威胁到他的兄弟、叔父。
帝王之路,从来都是孤独的,也是残酷的。
四、整军备粮,筹谋入关
崇德七年(1642年)正月,盛京皇宫张灯结彩,但喜庆中透着肃杀。
皇太极在崇政殿召集群臣,商议入关大计。洪承畴、范文程、宁完我等汉臣站在文官前列,多尔衮、豪格、济尔哈朗等亲王贝勒站在武将前列。
“去年松锦大捷,明军精锐尽丧,关外已无险可守。”皇太极开门见山,“如今李自成破洛阳,杀福王;张献忠陷襄阳,称襄王。明朝内忧外患,正是我大清入关良机。诸位说说,该如何用兵?”
豪格第一个站出来:“父汗,儿臣以为当直取山海关!山海关守将吴三桂,虽有关宁铁骑,但不过三万人。我大清八旗精锐十万,一鼓可下!”
洪承畴却摇头:“吴三桂虽年轻,但善守。山海关号称‘天下第一关’,城坚炮利,强攻必伤亡惨重。且关内明朝尚有数十万大军,若久攻不下,援军四集,我军危矣。”
“那洪先生有何高见?”豪格语气不善。他对这个汉人降将一直不服。
洪承畴不以为意,走到地图前:“臣以为,当绕道蒙古,破长城而入,直取北京。此乃当年陛下奇袭北京之策的扩大版。”
他指着地图:“明朝如今兵力,主要布防在三处:一是辽东,以防我大清;二是中原,以剿流寇;三是京畿,以卫京师。其中京畿兵力最弱,因崇祯以为有山海关天险,我大清不可能越过。”
“若我军绕道蒙古,从密云、古北口破长城,直逼北京,崇祯必调各路大军勤王。届时,山海关吴三桂、中原剿匪军,都会往北京集结。我军以逸待劳,可在京郊与明军决战。胜,则明朝灭亡;不胜,也可掠取京畿财富人口,全身而退。”
这番分析,条理清晰,考虑周全。连豪格都不得不承认,确实比自己“强攻山海关”的莽撞之策高明。
皇太极点头:“先生深谋远虑。但绕道蒙古,粮草补给如何解决?”
“因粮于敌。”洪承畴道,“京畿富庶,粮草充足。且我军破长城后,可分兵掠取州县,收集粮草。只要速战速决,补给不是问题。”
“那蒙古各部会配合吗?”
“会。”说话的是多尔衮,“臣弟西征时,已收服喀尔喀三部。如今蒙古诸部,皆奉皇上为共主。借道之事,只需一道旨意。”
皇太极沉吟片刻:“此策可行,但需精心准备。范文程。”
“臣在。”
“你负责粮草筹备,征集十万大军半年之粮。宁完我,你负责联络蒙古各部,确保借道顺利。洪承畴,你制定详细进军路线和作战计划。多尔衮、豪格,你们整顿八旗,加紧训练。”
“臣等遵旨!”
部署完毕,皇太极又道:“此战关乎国运,各部需同心协力。朕再说一遍:满汉蒙回,皆是大清子民;亲王贝勒,汉臣蒙将,皆为朕股肱。谁敢因私废公,排斥异己,严惩不贷!”
说这话时,他特意看了豪格一眼。豪格低头,不敢对视。
散朝后,皇太极独留洪承畴。
“先生刚才所言,朕深以为然。但朕还有一虑:若我军入关,李自成、张献忠等流寇趁虚而入,占了北京,如何是好?”
洪承畴笑了:“皇上,那反而是好事。”
“哦?”
“流寇者,乌合之众也。李自成虽拥兵数十万,但军纪败坏,不得民心。他若占了北京,必行烧杀抢掠之事,明朝遗臣百姓,必深恨之。届时皇上以‘吊民伐罪’之名入关,必得天下人心。”
皇太极恍然大悟:“先生是说,先让流寇与明朝相争,两败俱伤,我军再坐收渔利?”
“正是。”洪承畴道,“所以臣建议,入关之事不必太急。可先派细作潜入中原,散布谣言,说‘大清只讨明朝,不伤百姓’,让明朝君臣猜忌,让流寇坐大。待时机成熟,再一举入关。”
“妙计!”皇太极击掌,“先生真乃朕之子房(张良)!”
洪承畴谦道:“皇上过奖。臣只是尽本分。”
“不,你是真才实学。”皇太极感慨,“朕有时想,若崇祯皇帝能用你,何至于此?大明人才济济,却不能用,不敢用,真是自毁长城。”
洪承畴黯然。他想起明朝那些同僚,有的战死沙场,有的被冤杀,有的投降流寇……若崇祯皇帝有皇太极一半的胸襟,大明何至于此?
“皇上,”他忽然跪地,“臣有一请。”
“先生请讲。”
“若将来入关,破北京,请皇上勿杀崇祯皇帝,给他一个体面的结局。毕竟……他曾是臣的君上。”
皇太极肃然:“先生重情重义,朕敬佩。朕答应你,若擒获崇祯,必不杀他,可封为侯爵,颐养天年。”
“谢皇上!”洪承畴叩首,泪流满面。这是他为旧主求的最后一份恩典。
正说着,太监来报:“皇上,庄妃娘娘求见,说八阿哥病了。”
皇太极脸色一变:“快传!”
布木布泰匆匆进来,面色焦急:“陛下,福临发高烧,太医说可能是天花……”
“什么?”皇太极霍然站起,“朕去看看!”
他顾不上洪承畴,疾步往关雎宫去。洪承畴看着皇帝匆忙的背影,心中感慨:这位铁血帝王,也有如此柔软的一面。
关雎宫中,福临躺在小床上,小脸通红,呼吸急促。几个太医围在床边,束手无策。
“怎么样?”皇太极冲进来。
太医院院判跪地:“皇上,八阿哥确实出花了。若是寻常天花,臣等尚有把握。但八阿哥才一岁,体质弱,恐怕……”
“恐怕什么?说!”
“恐怕……凶多吉少。”
皇太极如遭雷击,踉跄后退,被布木布泰扶住。他想起海兰珠临终前的嘱托“照顾好咱们的福临”,心如刀绞。
“朕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,必须救活八阿哥!”他嘶声道,“若是救不活,你们……你们都陪葬!”
太医们吓得磕头如捣蒜。
布木布泰柔声劝道:“陛下息怒,太医们会尽力的。臣妾听说,出花的孩子,最需要父母陪伴。陛下不如在这里守着,给福临打气。”
皇太极点头,坐到床边,握住儿子滚烫的小手:“福临,父皇在这儿,你要挺住,一定要挺住……”
那一夜,皇太极守在儿子床边,寸步不离。他喂药、擦身、换衣,亲自照料。布木布泰陪在一旁,默默协助。
到天明时,福临的烧终于退了,脸上出现红疹——这是出花的正常过程。
太医诊脉后,喜道:“皇上,八阿哥挺过来了!只要精心调养,月余可愈!”
皇太极长舒一口气,瘫坐在椅子上,这才发现自己浑身都被汗水浸透了。
“陛下,您去歇歇吧,这儿有臣妾。”布木布泰道。
皇太极摇头:“朕就在这儿,等福临好了再说。”
他看着布木布泰,眼中满是感激:“这些日子,辛苦你了。”
“这是臣妾该做的。”布木布泰低头,“福临是宸妃姐姐留下的骨血,臣妾视如己出。”
这话让皇太极心中一动。他看着眼前这个聪慧沉稳的女子,忽然觉得,或许她可以填补海兰珠留下的空缺。
不是感情上的空缺——那份感情无人能替代。而是后宫主事、皇子教养上的空缺。哲哲皇后年事已高,精力不济。布木布泰年轻,有智慧,又疼爱福临,是最合适的人选。
“布木布泰,”他忽然道,“等福临好了,你就搬来清宁宫偏殿吧。方便照顾他,也方便……协助皇后处理宫务。”
布木布泰心中一喜,但面上保持平静:“臣妾遵旨。只是……这合规矩吗?”
“朕说合,就合。”皇太极摆摆手,“去吧,传朕旨意。”
“是。”
布木布泰退下时,嘴角终于忍不住上扬。搬入清宁宫偏殿,这是仅次于皇后的待遇。更重要的是,这意味着她可以更接近权力中心。
海兰珠死了,但后宫不会无主。而她布木布泰,已经走出了第一步。
窗外的天亮了,阳光照进关雎宫。福临在睡梦中呢喃,皇太极握着他的小手,心中百感交集。
海兰珠,你看见了吗?咱们的福临挺过来了。朕会好好培养他,让他成为大清的希望。
而你,就在天上看着吧。
看朕如何打下这个天下,看福临如何继承这个天下。
这是朕对你的承诺,也是对大清的承诺。
发表评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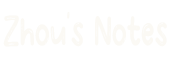





暂时没有评论,来抢沙发吧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