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三章:十三年不归家门
一、新婚别
涂山氏的春天来得早,二月梢头,村口的桃树已经绽出粉白的花苞。女娇坐在织机前,手中的梭子却停了。她望着窗外那条通往北方的小路,已经望了整整一个冬天。
“娇儿,又在想禹大人了?”母亲端着一碗热汤走进来,轻声叹息。
女娇回过神,接过汤碗,勉强笑了笑:“没有,只是在想这匹布的纹样。”
母亲在她身边坐下,抚摸着女儿日渐消瘦的脸颊:“别骗娘了。你和他定亲都一年了,就见过那么两次面。如今婚期将至,他却连封信都没有……要不,让你祖父去蒲阪问问?”
“不用。”女娇摇头,声音虽轻却坚定,“他说过,治水事大,不能分心。我不能去打扰他。”
话虽如此,但心里的思念像野草一样疯长。去年秋天定亲后,大禹只来过两封信,都是寥寥数语,说工程进展、说天气变化、说民工辛苦,唯独不提自己,也不提婚期。最后一封信是三个月前,说要在三门峡过冬,抢修关键河段,之后便音讯全无。
“可是婚期定在下月初八,只剩二十天了。”母亲忧心忡忡,“若他不来,这婚事……”
“他会来的。”女娇打断母亲的话,像是在说服自己,“他说过,一定会来娶我。”
窗外传来马蹄声。女娇心跳漏了一拍,扔下梭子冲到窗前。但来的不是大禹,是祖父涂山公和几个族人,刚从蒲阪回来。
“祖父!”女娇提着裙摆跑出去,“见到他了吗?他好吗?”
涂山公风尘仆仆,脸色凝重。他看了看孙女期待的眼神,欲言又止。
“祖父,您说啊。”
“见到了。”涂山公缓缓开口,“禹大人……很好。就是瘦了些,黑了些。”
女娇松了口气:“那婚期呢?他怎么说?”
涂山公沉默片刻,从怀中取出一封信:“这是他给你的。你自己看吧。”
女娇颤抖着手接过信。牛皮信封,盖着治水总指挥的泥封。她小心拆开,抽出里面的木简。字迹潦草,显然是在匆忙中写的:
“女娇卿卿:三门峡工程紧急,汛期前须完成关键段,余不能离。婚期可否推迟至秋后?若卿不愿等,可另择良配,余无怨言。禹顿首。”
短短几行字,女娇看了三遍,每看一遍,心就沉一分。推迟婚期?另择良配?他把她当什么了?
“娇儿……”母亲担心地唤她。
女娇抬起头,眼中没有泪,只有一种决绝的光芒:“祖父,我要去三门峡。”
“什么?”涂山公和母亲同时惊呼。
“我要去三门峡找他。”女娇一字一句地说,“既然他不能来娶我,我就去嫁给他。在那里成亲,在那里等他。”
“胡闹!”涂山公斥道,“三门峡是什么地方?荒山野岭,洪水猛兽,还有八万民工!你一个姑娘家去那里,成何体统?”
“我不管。”女娇倔强地说,“我是涂山氏的女儿,也是禹的未婚妻。他在哪里治水,我就在哪里安家。祖父,您从小就教我:女子要有主见,要敢为自己的人生做主。现在,这就是我的选择。”
涂山公看着孙女,这个从小被他捧在手心的姑娘,不知何时已经长大了,有了自己的主意和勇气。他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,想起了妻子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一无所有的自己的往事。
“你真想好了?”涂山公问。
“想好了。”
“不后悔?”
“不后悔。”
涂山公长叹一声:“好。那我送你。但不是你一个人去,我让阿虎带十个人护送你。到了那边,如果禹不认这门亲,你就回来,涂山永远是你的家。”
女娇跪下,给祖父磕了三个头:“谢谢祖父。”
三日后,一支小小的队伍从涂山出发了。十一个护卫,两辆牛车,一辆坐着女娇和侍女小翠,一辆装着嫁妆和给大禹带的衣物、药品、食物。女娇穿着红色的嫁衣——这是她亲手缝制的,原本准备在婚礼上穿,现在她决定一路穿着,直到见到大禹。
从涂山到三门峡,四百多里路,走了整整十天。越往北,景象越荒凉。洪水虽退,但留下的伤痕还在:被冲毁的村庄,荒芜的田地,枯死的树木。路上遇到的流民越来越多,个个面黄肌瘦,眼神麻木。
女娇的心揪紧了。她知道大禹在治水,但直到亲眼看到这片土地的苦难,才真正理解他肩上的担子有多重。
第十一天傍晚,队伍终于看到了黄河,听到了震耳欲聋的水声。前方是一片连绵的工棚,炊烟袅袅,人声鼎沸。三门峡工地到了。
护卫队长阿虎去找人通报。不一会儿,一个年轻官员匆匆赶来,看到女娇,愣了一下:“请问姑娘是……”
“我是涂山女娇,来找禹大人。”女娇平静地说。
年轻官员脸色一变:“姑娘稍等,我去禀报伯益大人。”
伯益正在帐篷里和大禹以及几个工程队长开会,讨论汛期应对方案。听到通报,他先是一愣,随即起身:“禹,你等等,我出去一下。”
“什么事?”大禹头也不抬,盯着桌上的工程图。
“是……涂山来人了。”
大禹手中的炭笔一顿,墨点洇开,染脏了图纸。他缓缓抬头:“谁?”
“女娇姑娘。”
帐篷里瞬间安静。几个工程队长面面相觑,识趣地告退。伯益也退了出去,留下大禹一个人。
大禹坐在那里,一动不动。心跳得厉害,手心出汗。他没想到女娇会来,更没想到她会在这个时候来。三门峡工程正在紧要关头,每天都有塌方危险,每天都有民工受伤。这里不是涂山,不是安乐园,是战场。
他应该生气,应该责备她不懂事。但心里却有一丝……欢喜?是的,欢喜。整整一年没见,他以为自己习惯了孤独,但听到她的名字,那份被压抑的思念如洪水决堤。
深呼吸几次,大禹起身,整理了一下满是尘土和汗渍的衣衫,走出帐篷。
夕阳下,女娇站在工棚外的空地上,一袭红衣如血,在灰黄的背景中格外刺目。她瘦了,但眼睛依然明亮,看到他时,那光芒更盛了。
两人隔着十步距离对视。风很大,吹乱了女娇的头发,也吹起了大禹的衣角。工地上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,远远看着这对奇怪的男女:一个满身泥泞的治水官,一个穿着嫁衣的美丽姑娘。
“你……”大禹先开口,声音沙哑,“你怎么来了?”
女娇走上前,一步,两步,直到能看清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,每一处晒伤的痕迹。他比去年更瘦了,眼窝深陷,嘴唇干裂,但眼神依然坚定。
“我来嫁给你。”女娇说,声音不大,但清晰,“你说婚期推迟,我等不了。你说另择良配,我不愿意。所以我来找你,在这里,现在,嫁给你。”
大禹喉咙发紧:“这里……太苦了。”
“我不怕苦。”
“太危险了。”
“你在哪儿,我就在哪儿。”
“我可能……给不了你安定的生活。”
女娇笑了,那笑容像春天的第一缕阳光:“我要的不是安定的生活,是你。”
大禹再也说不出话。他看着眼前这个勇敢的姑娘,这个愿意穿越四百里荒原来找他的姑娘,心中涌起滔天巨浪。九年的孤独,一年的思念,在这一刻都找到了归宿。
他伸出手,握住女娇的手。那手冰凉,但柔软。他的手粗糙,满是老茧,但他握得很轻,像捧着最珍贵的瓷器。
“好。”大禹只说了一个字,但足够了。
伯益走过来,眼中带笑:“既然新娘子都来了,那就办婚礼吧。简陋些,但热闹些,如何?”
大禹看向女娇,女娇点头:“简单就好。”
当晚,三门峡工地举行了有史以来最特殊的婚礼。没有高堂,没有喜轿,没有宴席。主婚人是伯益,证婚人是几个工程队长和涂山来的护卫。宾客是八万民工——他们围成一个大圈,中间燃起篝火。
女娇还是穿着那身红衣,大禹换上了女娇带来的干净衣服——虽然仍是粗布,但洗得很干净。两人跪在篝火前,向天地叩拜。
伯益高声念诵婚词:“皇天在上,后土在下,八万民工为证:今有禹与女娇,两情相悦,结为夫妻。不求同生,但求同难;不求富贵,但求同心。治水之路,风雨同舟;人生之途,携手同行。礼成!”
“礼成——”八万人齐声呼应,声震山谷。
民工们拿出珍藏的酒——其实只是兑了水的劣酒,但喝得畅快;拿出舍不得吃的肉干——其实只是咸得发苦的肉条,但吃得香甜。大家围着篝火唱歌跳舞,虽然调子不准,舞步杂乱,但真情实意。
女娇被几个女民工——她们是来给丈夫送饭的,顺便留下来帮忙——拉去跳舞。她起初害羞,但很快放开了,红裙在火光中旋转,像一朵盛开的牡丹。
大禹坐在一边看着,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。伯益走过来,递给他一碗酒:“喝吧,今天破例。”
大禹接过,一饮而尽。酒很辣,呛得他咳嗽。
“值得吗?”伯益问,“把人家姑娘带到这荒山野岭来。”
大禹看着火光中的女娇,轻声说:“是她选择了我。我会用一生对她好。”
“可你接下来要去勘察支流,可能几个月不回来。”伯益提醒,“新婚就分离,她会难过。”
大禹沉默。他知道伯益说得对。第二期工程要治理黄河支流,他必须亲自去勘察,制定方案。这一去,短则两三月,长则半年。可是……
“我会带她一起去。”大禹做出决定,“她是涂山氏的女儿,熟悉淮河水系,能帮上忙。而且,让她看看黄河支流的状况,她更能理解我在做什么。”
伯益想了想,点头:“也好。夫妻同心,其利断金。”
夜深了,篝火渐熄。民工们陆续散去,留下新人。大禹和女娇的“新房”是伯益临时腾出来的一个小帐篷,比工棚好些,但也简陋:一张木板床,一床薄被,一张小桌,两把木凳。
红烛是女娇带来的,只有一对,插在泥做的烛台上。烛光摇曳,映着两人的脸。
“委屈你了。”大禹说,“没有凤冠霞帔,没有十里红妆。”
女娇摇头,握住他的手:“有你就够了。”她看着他手上的老茧和伤痕,轻轻抚摸,“这些,都是治水留下的?”
“嗯。”大禹想抽回手,但女娇握得更紧。
“疼吗?”
“习惯了。”
女娇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瓷瓶,打开,里面是绿色的药膏:“这是涂山的伤药,我祖父配的,很有效。”她轻轻给他涂抹,动作温柔。
药膏清凉,女娇的手指柔软。大禹感到一股暖流从手心传到心里。九年来,他习惯了伤痛,习惯了独自舔舐伤口。第一次有人这样温柔地对待他。
“女娇,”他唤她,“嫁给我,你真的不后悔?”
女娇抬头,烛光在她眼中跳动:“后悔什么?后悔嫁了一个心里装着天下苍生的人?后悔嫁了一个宁愿自己吃苦也要治好黄河的人?不,我骄傲。”
她靠在他肩上,轻声说:“你知道吗,从第一次见你,听你说要十三年治水,我就知道,你是我要找的人。这世上大多数人,只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只想着眼前的安逸。但你不是。你心里装着整条黄河,装着千万百姓。这样的男人,值得我等,值得我跟。”
大禹搂住她,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。九年的孤独,在这一刻被填满了。
“可是接下来,我们要去勘察支流,会很苦。”他说,“风餐露宿,跋山涉水,还可能遇到危险。”
“你在哪儿,我就在哪儿。”女娇重复这句话,像誓言,“我会做饭,会洗衣,会包扎伤口,还会记录绘图——我读过书,能帮你。我不是累赘,是帮手。”
大禹笑了,真正的笑,从心底溢出来的笑:“好,那我们就一起去。夫妻同心,治好黄河。”
那一夜,简陋的帐篷里,红烛燃到天明。外面,黄河水声依旧,但听起来不再那么狂暴,像在为这对新人祝福。
新婚第三天,大禹和女娇就出发了。伯益留在三门峡主持后续工程,大禹带着一支二十人的勘察队,开始对黄河主要支流进行系统勘察。
第一站,汾河。
二、汾河泪
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,发源于管涔山,纵贯山西,流域内土地肥沃,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。但近年来,汾河水患频发,尤其是中下游,几乎年年泛滥。
勘察队沿着汾河向北走。女娇果然如她所说,不是累赘。她会记录水文数据,会绘制简单的地形图,会照顾伤员,还会用草药治病。民工们起初对这个“总指挥夫人”有些拘谨,但很快发现她平易近人,干活麻利,都亲切地叫她“禹夫人”。
但女娇也看到了更多苦难。汾河流域的灾情比黄河干流更触目惊心。因为是小流域,朝廷关注少,地方部落自救能力弱,一旦发水,往往整村整村被淹。
在一个叫“杏花村”的地方,女娇遇到了一个让她终身难忘的老人。
那是抵达汾河中游的第七天。连续大雨,河水上涨,勘察队被困在一个高地上。雨稍停时,女娇去附近的村子找食物补给。村子大半被淹,只有几户人家还坚守在屋顶上。
一个老妇人坐在自家屋顶,怀里抱着一个婴孩,一动不动,像尊雕像。女娇划着小船靠近,问她需要帮助吗。
老妇人缓缓抬头,眼神空洞:“姑娘,有吃的吗?孩子饿。”
女娇把随身带的干粮递过去。老妇人接过,先喂孩子,自己只啃了一小口。喂完孩子,她突然哭了:“这娃,不是我家的。我家的……都没了。”
在断断续续的讲述中,女娇知道了老人的故事:她姓孟,丈夫早逝,独自拉扯三个儿子长大。儿子们成家后,都住在同一个村,孝顺和睦。去年汾河发水,大儿子为了救邻居家的孩子,被冲走了;今年水又来了,二儿子和三儿子带着家人往高地撤,她腿脚慢,落在后面。洪水来得急,她眼看二儿子一家被卷走,三儿子回头救她,也被冲走了。
“就剩我一个老婆子,活够了。”孟婆婆喃喃道,“可是这娃……”她看着怀里的婴孩,“他娘把他塞给我,说‘婆婆,带娃走’,自己就被水冲走了。我不认识这家人,只知道娃叫石头,才八个月。”
女娇泪流满面。她接过孩子,小小的身体轻得像片叶子,但还活着,还知道吮吸手指。
“婆婆,跟我们走吧。”女娇说,“我们是大禹治水队的,能照顾你们。”
孟婆婆摇头:“我老了,走不动了。姑娘,你把这娃带走,给他条活路。我……我在这儿等我的儿孙,他们要是活着,会回来找我的。”
无论怎么劝,老人都不肯走。女娇只能留下更多食物和药品,抱着孩子回到勘察队驻地。
大禹听完女娇的讲述,沉默了很久。他走到高处,望着浑浊的汾河,拳头握得紧紧的。
“这样的悲剧,每天都在发生。”他对女娇说,也像对自己说,“只治干流不够,支流不治,百姓照样受苦。”
“那怎么办?”女娇问,“支流这么多,我们顾得过来吗?”
“顾不过来也要顾。”大禹说,“但要改变方法。不能每一条河都像黄河一样大动干戈,要因地制宜,发动当地百姓。”
他召集勘察队开会,提出了一个新想法:在汾河流域试点“以工代赈、民众自洽”的治理模式。
“具体来说,”大禹解释,“朝廷提供技术指导和部分物资,当地百姓出工出力,治理自己的河流。治理后的农田、鱼塘、林地,归参与者所有。这样既治了水,又安了民,还节省了朝廷的人力物力。”
“可是当地部落首领愿意吗?”有人问。
“去做工作。告诉他们:要么年复一年被水淹,要么花一两年时间治理,一劳永逸。”大禹说,“女娇,你跟我去各部落游说。你是涂山氏的女儿,又是我夫人,说话有分量。”
女娇有些紧张:“我能行吗?”
“你能行。”大禹握住她的手,“你善良,真诚,能理解百姓的苦。而且,你是女子,有些话,女子说比男子说更让人信服。”
接下来的一个月,大禹和女娇走访了汾河流域十七个部落。女娇果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。她不像大禹那样严肃,她会抱着石头(她给那婴孩取的名字),跟部落的妇女们拉家常,说治水后能过上的好日子;她会给孩子分糖块——那是她从涂山带来的,一直舍不得吃;她会教妇女们认草药、做腌菜。
人心都是肉长的。看到治水总指挥的夫人如此平易近人,看到她不嫌脏不嫌累地帮忙,部落百姓渐渐被打动了。加上大禹承诺的技术和物资支持,大多数部落同意参与治水。
但有一个部落例外:黑山部落。
黑山部落位于汾河上游,以狩猎为生,民风彪悍。他们的首领黑山魁是个四十多岁的壮汉,脸上有一道刀疤,据说年轻时徒手打死过熊。他对大禹的提议嗤之以鼻。
“治水?我们黑山人不种地,不发水更好,鱼多!”黑山魁瓮声瓮气地说,“而且,凭什么要我们出人出力?下游的人受益,我们上游的人白干?”
大禹耐心解释:“黑山首领,水患不只是淹田地。山洪暴发时,你们的猎场也被冲毁,山路也被阻断。治理汾河,上游植树固土,减少山洪,对你们也有好处。”
“好处?什么好处?”黑山魁冷笑,“你说治理后分地,我们黑山人不要地,我们要猎物。你能保证治理后猎物更多吗?”
这个问题把大禹问住了。治水确实不能直接增加猎物。
女娇站出来,柔声说:“黑山首领,我祖父是涂山公,我们涂山氏也狩猎。我知道猎人的心思:猎物多不多,看山林好不好;山林好不好,看水土好不好。如果年年山洪,树被冲走,土被冲走,猎物自然会少。治理汾河,保住了山林,长远看,猎物只会更多。”
黑山魁看着女娇,语气稍缓:“夫人说得有道理。但长远是多久?三年?五年?我的族人要吃饭,等不起。”
“那这样如何?”女娇想了想,“治理期间,黑山部落的壮劳力参与治水,朝廷按日发粮,保证不比狩猎收入少。老人、妇女、孩子可以学习种植、养殖,作为补充。等治理完成,如果三年内猎物没有增加,朝廷补偿你们损失。”
这个提议很公平。黑山魁沉思良久,终于点头:“夫人爽快,我黑山魁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好,我们加入。”
说服了最难啃的骨头,其他部落更不成问题。汾河治理工程顺利启动,大禹留下两名助手指导,自己则带着勘察队继续北上,勘察其他支流。
临别时,孟婆婆所在的杏花村已经开始了河道清淤。老人还是不肯离开,但女娇把石头托付给村里一户好心人家抚养,定期送粮食和衣物。孟婆婆每天坐在村口的高地上,看着民工们干活,眼神不再空洞,有了一丝光亮。
“她在等。”女娇对大禹说,“等这条河治好,等她的儿孙能安息。”
大禹望着老人孤零零的背影,轻声说:“我们会治好这条河的。为了孟婆婆,为了石头,为了千千万万这样的人。”
勘察队继续前行。女娇变得更加坚强,也更加理解大禹的事业。她不再只是他的妻子,更是他的战友,他的知音。白天,他们一起跋山涉水,测量记录;晚上,他们挤在小帐篷里,讨论方案,绘制地图。虽然艰苦,但充实。
有一次,女娇问大禹:“你说,治水最难的是什么?”
大禹想了想:“不是技术,不是人力,是人心。要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,眼前的苦能换来长久的甜;要让不同利益的人放下争执,同心协力;要让一代人付出,造福几代人。这很难。”
“但你在做。”女娇握住他的手。
“因为必须有人做。”大禹说,“我父亲失败了,但留下了一个教训:堵不如疏。我要证明他是对的,要用成功告慰他的在天之灵,也要给天下人一个希望——灾难可以战胜,生活可以变好。”
女娇靠在他肩上:“我陪你。不管多少年,不管多难,我都陪你。”
帐篷外,汾河的水声潺潺,不再狂暴,像在低语,诉说着这片土地千年的苦难和希望。
三、三过家门
治水第四年秋,大禹和女娇有了第一个孩子。
那时他们正在洛水流域勘察。洛水是黄河第三大支流,流经洛阳盆地,这里地势低洼,水患尤为严重。女娇怀孕六个月了,本不该再跟着跋涉,但她坚持:“我能行。而且,孩子在肚子里就跟着父母治水,将来定是个有担当的。”
大禹拗不过她,只能更加小心地照顾。他学会了熬安胎药,学会了按摩浮肿的腿,甚至学会了缝小衣服——虽然针脚粗得像蚯蚓,但女娇宝贝得不得了。
孩子出生在洛水边的一个小村子里。那天下着大雨,女娇突然发作。村里没有产婆,大禹急得团团转,最后是村里的老妇人帮忙接生。
是个男孩,哭声洪亮,像洛水的涛声。大禹抱着儿子,手在颤抖,这个在洪水面前面不改色的男人,此刻却慌得不知所措。
“像你。”女娇虚弱地说,脸上带着幸福的笑。
大禹看着儿子皱巴巴的小脸,确实像自己:方脸,浓眉,高鼻梁。他给儿子取名“启”,寓意开启新篇,也寓意治水事业后继有人。
“希望他将来,能继承我们的事业。”大禹说。
“一定会的。”女娇握住他的手,“他是治水的孩子。”
有了孩子,生活更加艰难,但也更加温暖。小启很乖,很少哭闹,跟着父母辗转各地。女娇用背带把他背在胸前,继续帮忙记录、绘图、照顾伤员。民工们喜欢这个“小总指挥”,常常逗他玩,省下自己的口粮给他做米糊。
治水第五年春,大禹接到伯益急报:黄河干流二期工程遇到难题,需要他回去主持。那时他们正在伊水勘察,离家(涂山)只有不到一百里。
“你先回家看看父母吧。”大禹对女娇说,“带着启,在家住段时间。我去处理完就回来接你们。”
女娇摇头:“我跟你一起去。启还小,离不开我。”
“可是这一去,又是几个月。你已经五年没回家了。”大禹心疼地说。他知道女娇想家,常常在夜里偷偷流泪,但白天从不表现出来。
“治水要紧。”女娇还是那句话,“等治好了,我们再一起回家。”
大禹说服不了她,只能同意。队伍继续北上,路过涂山时,大禹特意绕道村口,让女娇远远看一眼家乡。
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,涂山村掩映在粉白的花海中,宁静祥和。女娇抱着启,站在山岗上,望着自家的屋顶,久久不动。
“娘在那里。”她轻声对怀里的孩子说,“外祖父,外祖母,舅舅,姨娘……都在那里。等爹治好了黄河,我们就回来,再也不走了。”
小启听不懂,只是伸出小手,想去抓飘落的花瓣。
女娇的眼泪终于掉下来,滴在孩子脸上。大禹站在她身后,手放在她肩上,无言地安慰。
“走吧。”女娇抹去眼泪,转身,“别耽误行程。”
那是他们第一次过家门而不入。
治水第七年,大禹负责的渭水治理工程进入关键期。渭水是黄河最大支流,流经关中平原,这里土地肥沃,但河道紊乱,泥沙淤积严重。大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:裁弯取直,开挖新河道。
工程需要大量人力,大禹从周边部落抽调了五万民工。他自己吃住在工地,日夜督工。女娇带着已经两岁的启,在工地附近安了个小家——其实只是个茅草棚,但收拾得干净温馨。
那天,大禹正在新河道上指挥开挖,突然有信使从涂山来,说涂山公病重,想见孙女最后一面。
女娇当场就哭了。祖父最疼她,她的医术、学识、勇气,都是祖父教的。可是现在……
“回去吧。”大禹说,“我让人护送你,快马加鞭,三天就能到。”
“可是工程……”女娇看着忙碌的工地,看着满脸泥泞的民工,看着大禹熬红的双眼。
“工程有我。”大禹握住她的肩膀,“祖父的事大。你放心去,这里有我。”
女娇犹豫再三,还是决定回去。她收拾了简单的行李,抱着启,跟着信使上路。走到半路,突然下起暴雨,山路塌方,无法通行。他们在路边的小店困了两天,雨停后继续赶路,但速度慢了许多。
第五天,他们终于到了涂山。还没进村,就听到了哭声。女娇的心沉了下去。
涂山公已经在前一天去世了。临终前,他一直念着女娇的名字,说“我的娇儿,怎么还不回来”。
女娇跪在灵前,哭得几乎昏厥。母亲抱着她,也哭成泪人:“娇儿,你祖父一直想看你最后一眼,一直等,一直等……”
“我回来了,祖父,我回来了……”女娇一遍遍重复,但那个疼她的老人,再也听不到了。
处理完丧事,女娇在涂山住了半个月。母亲劝她留下:“娇儿,别走了。治水是男人的事,你一个女人,带着孩子,太苦了。留在涂山,娘照顾你们。”
女娇看着熟悉的家,看着年迈的母亲,看着幼小的孩子,确实动摇了。这些年,她跟着大禹风餐露宿,吃了太多苦。如果留在涂山,至少能安稳度日。
但夜里,她梦见了大禹。梦见他独自在工地上,面对难题眉头紧锁;梦见他对着黄河发呆,背影孤独;梦见他抱着启,教他认治水图……
醒来时,泪湿枕巾。她知道,她放不下他。
“娘,我要回去。”女娇对母亲说,“他在等我,工程在等我。祖父教过我:做人要有始有终。我选择了这条路,就要走到底。”
母亲知道劝不住,只能含泪为她准备行装,塞满了吃的用的,还派了十个族人护送。
回程路过蒲阪,女娇听说大禹的渭水工程遇到塌方,死伤数十人,朝廷有人弹劾他急功近利。她心急如焚,日夜兼程赶回渭水工地。
到了才发现,情况比她想象的更糟。新河道开挖到一半,遇到坚硬岩层,爆破时引起山体滑坡,不仅毁了已挖的河道,还掩埋了一个工棚,三十多人遇难。大禹被朝廷问责,工程暂停,民工士气低落。
女娇找到大禹时,他正独自坐在河边,望着浑浊的河水,一动不动,像尊石像。才一个月不见,他瘦了一圈,胡子拉碴,眼窝深陷。
“禹。”女娇轻声唤他。
大禹缓缓转头,看到女娇和启,眼中闪过一丝光亮,但很快又黯淡下去:“你回来了。祖父……还好吗?”
“祖父走了。”女娇忍住泪,“但他走前说,让我告诉你:治水如行医,急不得,躁不得。要沉心静气,对症下药。”
大禹闭上眼睛,许久,睁开时有了泪光:“我对不起那些死去的民工。是我太急,想快点完成,结果……”
“不是你的错。”女娇蹲下身,握住他的手,“治水本就危险,有牺牲在所难免。重要的是,我们不能让牺牲白费。”
她把启抱到大禹面前:“看看儿子,他在等你。看看那些还活着的民工,他们在等你。你不能垮。”
小启伸出小手,摸父亲的脸:“爹,不哭。”
大禹抱住儿子,肩膀微微颤抖。这个在洪水面前从不退缩的男人,此刻却脆弱得像孩子。
女娇没有劝,只是静静陪着他。她知道,他需要发泄,需要释放压力。
第二天,大禹重新振作。他召开全体民工大会,当众认错,承诺改进方案,加强安全措施。他亲自去慰问遇难者家属,发放抚恤,承诺照顾他们的老人孩子。他调整了工程方案,绕过岩层,虽然工期延长,但更安全。
民工们看到总指挥敢于担当,不推卸责任,反而更加信服他。工程重新启动,士气逐渐恢复。
女娇则组织妇女队,负责后勤、医护、安抚家属。她用自己的温柔和坚韧,抚平了工地的创伤。
那是他们第二次与家相关的艰难抉择。女娇为了大禹,错过了见祖父最后一面;大禹为了治水,承受了生命的重量。
治水第十年,大禹负责的黄河下游治理进入收尾阶段。这是最难的一段,因为下游河道高于地面,形成“悬河”,堤防压力巨大。大禹提出了“宽河固堤”的方案:拓宽河道,降低水位;加固堤防,预防溃决。
工程需要从淮河流域调运大量石料,涂山是重要的中转站。那年秋天,大禹和女娇带着已经五岁的启,护送一批石料南下,路过涂山。
这是启第一次回外祖母家。小家伙很兴奋,一路上问个不停:“娘,外祖母家真有那么多桃树吗?”“舅舅会带我抓鱼吗?”“我能见到祖父吗?”——他指的是涂山公的坟墓。
女娇耐心回答,心中百感交集。十年了,她只回过一次家,还是因为祖父去世。母亲老了,身体不好,信中常说想她,想外孙。
到了涂山,母亲早早等在村口。看到女儿和外孙,泪如雨下。她抱着启,左看右看,怎么也看不够:“像,真像禹大人。这眉眼,这鼻子……”
启有些怕生,但很快被舅舅姨娘们哄熟了,跟着表哥表姐们满村跑,抓鱼摘果,不亦乐乎。
家里准备了丰盛的宴席,亲戚们都来了,热闹得像过年。大禹被灌了不少酒,脸都红了。女娇坐在母亲身边,听她絮絮叨叨说这十年的家长里短:谁家儿子成亲了,谁家女儿出嫁了,谁家老人去世了,谁家添了新丁……
“娇儿,这次多住些日子吧。”母亲拉着她的手,“你看启多开心,这才是孩子该过的日子。你们常年在外,孩子都跟着受苦。”
女娇看着院子里玩耍的启,确实,儿子在涂山比在工地快乐多了。工地没有玩伴,只有民工和工具;工地没有桃树鱼塘,只有泥土和石头。
她动摇了,看向大禹。大禹也在看她,眼中有关切,有理解,也有不舍。
宴席散去,夜深人静。夫妻俩在房里说话。
“你想留下,对吗?”大禹先开口。
女娇点头,又摇头:“我想留下,但更想跟你在一起。禹,我们十年没在家好好住过了。启五岁了,还没正经读过书,没好好玩过。我娘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我想多陪陪她。”
大禹沉默。他知道女娇说得对。治水十年,他欠家人太多。女娇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姑娘,变成能吃苦能扛事的妇人;启从出生就在颠沛流离中长大。作为丈夫,作为父亲,他不合格。
“那你就留下吧。”大禹做出决定,“带着启,在家住一年。等我完成下游工程,就来接你们。”
“那你呢?”
“我继续治水。伯益在那边主持,我需要回去。”大禹说,“你放心,我会照顾好自己。”
女娇哭了:“我不想跟你分开。”
“我也不想。”大禹搂住她,“但这是为了你们好。启该读书了,你该休息了。一年,很快的。”
那一夜,两人都没睡好。第二天,大禹要走了。石料已经装船,必须按时运到工地。
启抱着父亲的腿不让走:“爹,你别走,你说要带我去抓大鱼的!”
大禹蹲下身,摸摸儿子的头:“爹要去治水,等治好了,带你去抓最大的鱼。在家听娘的话,听外祖母的话,好好读书,好吗?”
启似懂非懂地点头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女娇送大禹到河边。千言万语,不知从何说起。
“写信。”大禹说,“每月一封,告诉我你们的情况。”
“你也是。”女娇哽咽,“注意身体,别太累。”
“嗯。”大禹上了船,回头看了最后一眼。女娇和启站在岸边,晨雾中,像一幅水墨画。
船开了,越来越远。女娇终于忍不住,放声大哭。启也跟着哭:“娘,爹什么时候回来?”
“一年。”女娇抱紧儿子,“一年后就回来。”
那是他们第三次与家有关的离别。为了孩子,为了老人,他们选择了短暂的分离。
但谁也没想到,这一年,会发生那么多事。
四、伯益的坚守
大禹回到下游工地时,伯益已经忙得焦头烂额。
“你可算回来了!”伯益见到大禹,像见到救星,“出大事了!”
“慢慢说。”
伯益喘了口气:“三件事。第一,齐国部落拒绝出工,说我们占了他们的猎场;第二,漕运河道淤塞,石料运不过来;第三,也是最麻烦的——朝廷有人弹劾你,说你治水十年,耗费巨大,成效不显,要求换人。”
大禹眉头紧锁。前两个是工程问题,好解决;第三个是政治问题,棘手。
“弹劾的是谁?”
“御史大夫杜康,还有几个老臣。”伯益说,“他们联名上奏,说十年治水,动用民工百万,耗费粮食千万石,但黄河还是年年泛滥。说你劳民伤财,无功有过。”
大禹冷笑:“他们只看到耗费,没看到成果。十年间,我们治理了三千里的河道,开挖了五百条泄洪渠,加固了八百里堤防。虽然黄河还没完全治好,但水患面积减少了七成,死亡人数减少了九成。这些他们看不到吗?”
“看到了,但装看不到。”伯益叹息,“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立功,尤其你还是戴罪之身(指鲧的儿子)。而且,十年确实太长了,很多人失去了耐心。”
“舜帝什么意思?”
“舜帝是支持你的,但压力很大。朝中分成两派:一派支持继续治水,以皋陶为首;一派要求停止,以杜康为首。舜帝虽然信任你,但也不能完全无视朝议。”
大禹沉思片刻:“我需要回蒲阪一趟,亲自向舜帝和朝臣说明情况。”
“现在?”伯益惊讶,“工程正在紧要关头,你走了,这里怎么办?”
“你主持。”大禹看着伯益,“这十年,你一直是我的副手,能力、威望都足够。我相信你。”
伯益愣住了。十年来,他一直是大禹的助手,从没想过独当一面。但看到大禹信任的眼神,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,也感到一种责任感。
“好。”伯益郑重答应,“你放心去,这里有我。”
大禹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兄弟,拜托了。”
简单交代了工作,大禹带着几个随从,快马加鞭赶回蒲阪。七天七夜,几乎没怎么休息,到达蒲阪时,人都瘦脱了形。
舜帝在偏殿接见他,皋陶、杜康等重臣在座。
“禹,你回来了。”舜帝看起来苍老了许多,但眼神依然清明,“伯益把事情都告诉你了吧?”
“是。”大禹行礼,“臣这次回来,就是要向陛下和诸位大人说明治水情况。”
杜康冷哼一声:“有什么好说明的?十年,百万民工,千万石粮,结果呢?去年下游还是淹了三个部落!这就是你的成效?”
大禹平静回应:“杜大人,治水如治病,重症需用猛药,久病难求速愈。黄河之患积千年,岂能十年根治?但十年间,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。”
他展开带来的地图和账册:“请看,这是十年治水的成果统计:治理河道三千里,开挖泄洪渠五百条,加固堤防八百里。水患面积从每年淹没百万亩,减少到三十万亩;死亡人数从每年数千人,减少到数百人。更重要的是,我们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的治水方法,培养了上万名治水人才,这些是无价之宝。”
杜康语塞,但还是强辩:“那耗费呢?百万民工,十年不事生产,朝廷要养他们;千万石粮,都是从各部落征收的,百姓负担沉重!”
“杜大人可知,如果不治水,每年水患造成的损失是多少?”大禹反问,“淹没的农田、冲毁的房屋、死亡的人口,这些损失,十年累计,远超治水耗费。而且,治水工程本身也创造了价值:新开垦的农田、新建的村庄、新挖的鱼塘,这些都会在未来产生收益。”
他转向舜帝,诚恳地说:“陛下,治水不是消费,是投资。我们现在投入,是为了子孙后代永享安宁。就像种树,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。如果因为眼前困难就放弃,那才是真正的劳民伤财——之前的投入都白费了,水患依旧,百姓依旧受苦。”
舜帝点头:“禹说得有理。治水是百年大计,不能只看眼前。”
皋陶也支持:“陛下,老臣曾去工地视察,亲眼看到禹和民工同吃同住,看到工程确实有效。十年成果,来之不易,应该继续支持。”
杜康等人还想争辩,舜帝抬手制止:“不必说了。朕意已决:治水工程继续,禹仍为总指挥。但禹,朕也要给你一个期限:再给你三年,三年内,必须让黄河主干道不再大规模泛滥。能做到吗?”
三年,很紧,但大禹没有选择。
“臣,领旨。”他跪下接旨。
离开宫殿,皋陶叫住大禹:“禹,三年时间,你真的能做到?”
大禹苦笑:“做不到也要做。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”
“需要什么支持,尽管说。”皋陶说,“老夫虽然老了,但在朝中还有几分薄面。”
“谢谢皋陶大人。”大禹感激地说,“我需要两样东西:第一,朝廷继续提供粮草物资;第二,赋予伯益更大的权力,我不在时,他可以全权处理工地事务。”
“准。”皋陶点头,“你放心去做,朝中的事,老夫替你挡着。”
有了舜帝和皋陶的支持,大禹心中稍定。但他知道,真正的考验在工地,在黄河。
他没有在蒲阪多待,第二天就启程返回。路过涂山时,他犹豫了一下,还是没进去。时间紧迫,他不能在温柔乡里耽搁。
只是让随从送了一封信给女娇,简单说明了情况,让她安心在家,等他三年。
女娇收到信,又是担心又是骄傲。担心大禹的身体和压力,骄傲自己的丈夫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。她给大禹回信,只有八个字:“君且前行,妾自安好。”
她把所有的思念和担忧都压在心底,专心照顾启,教导他读书识字,给他讲父亲治水的故事。
“爹是个英雄。”女娇常常对启说,“他在做一件很伟大很艰难的事。我们要支持他,理解他。”
启似懂非懂,但记住了:父亲在治水,在拯救很多人。
而工地上,伯益果然不负所托。在大禹回蒲阪期间,他妥善处理了齐国部落的纠纷——答应治理完成后,将新开垦的猎场优先分配给他们;解决了漕运问题——组织民工清淤,开辟了新航道;稳住了民工士气——宣布朝廷继续支持治水,三年内必有成果。
大禹回来后,看到井然有序的工地,对伯益刮目相看:“伯益,你长大了。”
伯益笑:“跟你十年,再不长进,就白跟了。”
两人携手,开始了最后的冲刺。三年,一千多个日夜,他们要完成黄河主干道的全面治理。
这三年,是大禹治水生涯中最艰苦的三年,也是成果最丰硕的三年。
五、最后一里
治水第十三年春,最后的工程——黄河入海口疏浚——开始了。
这是最难啃的硬骨头。入海口泥沙淤积严重,潮汐作用复杂,工程条件恶劣。但只有疏通入海口,黄河水才能顺畅入海,下游的“悬河”问题才能根治。
大禹和伯益亲自坐镇。八万民工,分成三班,日夜不停。工具损耗极大,每天都有上百把铁锹、铁镐报废;民工伤病极多,海水浸泡,盐碱侵蚀,很多人皮肤溃烂;气候恶劣,时常有风暴,工程几度中断。
最严重的一次,是那年夏天的台风。狂风暴雨,巨浪滔天,刚挖好的河道被重新淤塞,工棚被掀翻大半,数百人受伤,二十多人失踪。
风暴过后,工地一片狼藉。民工们垂头丧气,有人甚至偷偷逃跑。
大禹站在废墟上,浑身湿透,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十三年了,最后的关头,却遭遇这样的打击。
“禹,怎么办?”伯益声音沙哑,“粮食被冲走大半,工具损失严重,民工士气低落。朝廷要是知道,恐怕……”
“不能放弃。”大禹咬牙,“十三年的努力,不能毁于一旦。”
他召集所有民工,站在高处,大声说:“兄弟们,我知道大家很苦,很累,想家了。我也一样。我离开家十三年,妻子在家等我,儿子已经八岁了,我都没好好陪过他。”
人群安静下来。
“但我想问问大家:十三年前,我们为什么来这里?是为了混口饭吃吗?是为了朝廷的奖赏吗?不,我们是来治水的,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不再受水患之苦,是为了让我们的父母能安度晚年,是为了让我们的妻子不再担惊受怕!”
他指着远处的黄河:“看看这条河,它夺走了我们多少亲人的生命,毁掉了我们多少家园!今天我们在这里受苦,是为了明天千千万万的人不再受苦!今天我们的汗水,会换来明天孩子们的笑脸!”
“风暴可怕吗?可怕!但比风暴更可怕的,是放弃!我们的父辈、祖辈,面对水患只能逃跑、只能祈祷。但我们不一样,我们在战斗,在改变!如果我们现在放弃,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?对得起在家等我们的亲人吗?对得起我们十三年的汗水吗?”
“不能!”一个老民工喊道。
“不能!”更多人响应。
“那怎么办?”大禹问。
“继续干!”八万人齐声怒吼,声震海天。
士气重新点燃。大禹和伯益重新规划,调整方案。工具不够,就用木器、石器;粮食不足,就组织捕鱼、采集;人手不够,就提高效率,轮班休息。
女娇在涂山听到消息,坐不住了。她把启托付给母亲,带着涂山氏的一百青壮年和十车物资,赶赴入海口。
见到大禹时,她几乎认不出他。他瘦得脱了形,眼窝深陷,颧骨突出,头发花白了一半——他才四十岁啊。
“你……”女娇泪如雨下。
大禹却笑了,抱住她:“你来了,真好。”
女娇的到来,像一股春风。她组织妇女队,负责后勤、医护;她用自己的温柔,抚慰伤员;她甚至亲自下厨,给民工们做家乡菜。涂山氏的物资也解了燃眉之急。
最重要的是,她带来了启的消息。
“启会背诗了,第一首就是《治水谣》。”女娇说,“他问我:爹什么时候回来?我说:等治好黄河就回来。他说:那我要快点长大,帮爹治水。”
大禹眼睛湿润了:“好儿子。”
有了家人的支持,大禹干劲更足。最后的工程,虽然艰难,但稳步推进。
那年秋天,最后的拦河坝被拆除,黄河水顺着新疏通的河道,奔腾入海。水流顺畅,不再淤积,不再倒灌。
成功了。
十三年,四千七百多个日夜,百万民工,千万石粮,终于换来了这条大河的驯服。
竣工那天,没有盛大的庆典,只有八万民工站在河岸上,默默看着河水东流。很多人哭了,哭得像个孩子。这十三年的苦,十三年的累,十三年的牺牲,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。
大禹和伯益并肩站着,也泪流满面。
“我们做到了。”伯益哽咽。
“我们做到了。”大禹重复。
他想起父亲鲧,想起他临终前说的“疏导”;想起舜帝的信任;想起皋陶的支持;想起女娇的等待;想起启的期盼;想起千千万万民工流过的汗水和鲜血。
这一切,都值得。
当天晚上,大禹在油灯下写最后一封工程日志:
“十三年又三月,黄河治水工程全面完成。主干道疏通,支流治理,堤防加固,泄洪体系建成。虽不敢言永绝水患,但可保百年安宁。百万民工,功不可没;朝廷支持,铭记于心。禹今可告慰先父在天之灵:疏导之道,行之有效;治水大业,后继有人。”
写完,他拿出女娇送的香囊,已经破旧,但依然珍藏着。
“明天,我们回家。”他对伯益说。
伯益点头:“回家。”
第二天,大禹和伯益开始组织民工返乡。按照《治水章程》,所有参与治水的人,按出工时间和贡献,分配土地、粮食、工具。很多民工拿到了地契——那是他们一辈子都不敢想的财富。
临别时,民工们纷纷来向大禹告别。
“大人,谢谢您!”
“大人,保重身体!”
“大人,以后来我们部落,我请您喝酒!”
大禹一一回应,心中温暖。这十三年,他失去了很多——青春、健康、与家人团聚的时光。但他得到的更多——千万百姓的安居,一条大河的驯服,还有这群生死与共的兄弟。
最后一批民工离开后,大禹和伯益也收拾行装。女娇已经先回涂山准备,他们直接回蒲阪向舜帝复命。
路过涂山时,大禹终于走进了那个离别十三年的家门。
村口,桃花又开了。女娇牵着启,站在花树下等他。
启已经八岁,个子到大禹的腰了。他有些怯生生地看着这个陌生的父亲,但眼中充满崇拜。
“启,叫爹。”女娇轻声说。
启走上前,仰头看着大禹,脆生生地喊:“爹。”
大禹蹲下身,抱住儿子,眼泪夺眶而出:“哎,爹回来了。”
女娇走过来,三人抱在一起。桃花瓣纷纷扬扬,落在他们身上,像一场迟到了十三年的花雨。
“我们回家。”女娇说。
“回家。”大禹重复。
夕阳西下,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,终于重叠在一起。身后,黄河静静东流,不再咆哮,像在吟唱一曲无声的赞歌。
十三年的离别,十三年的坚守,十三年的牺牲,在这一刻,都有了答案。
发表评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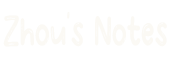





暂时没有评论,来抢沙发吧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