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四章:划定九州禅让位
第十四章:划定九州禅让位
洪水退去的第七个春天,冀州平原上重新长出了青青的麦苗。
禹站在新筑的观星台上,远眺着这片曾经被浊浪吞噬的土地。十三年的风霜在他脸上刻下了沟壑般的皱纹,那双踏遍九州山河的脚上,老茧层层叠叠,像是岁月烙下的地图。
“伯益,你看。”禹的声音沙哑而沉稳,他指向远方,“那里曾是洪水最深的地方,深达三丈。我们开凿的河道,如今已成了渔歌唱晚的水路。”
伯益站在禹身侧,手中捧着厚厚一卷兽皮地图。这位跟随禹治水十三年的助手,鬓角也已斑白。他展开地图,上面用朱砂和墨汁勾勒着蜿蜒的河流、起伏的山脉,还有九个用象形文字标注的区域——这正是他们走遍天下、以双脚丈量出的“九州”雏形。
“冀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徐州、扬州、荆州、豫州、梁州、雍州。”伯益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,“每州的边界,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的山川形胜。只是……”
“只是什么?”禹转过身,目光如炬。
伯益叹了口气:“划分九州易,让各部落首领接受这划分却难。有些部落世代居住之地,如今被划到了不同州界。神农氏后裔的姜氏长老前日来找我,说他们的猎场被雍州和梁州一分为二,族人打猎都要跨州而行,实在不便。”
禹沉默片刻。春风吹动他兽皮衣袍的下摆,那上面还沾着治水时留下的泥点——他坚持不让妻子涂山氏清洗这些痕迹,说这是天下的印记。
“召集九州诸侯吧。”良久,禹缓缓开口,“就在这冀州平原,在洪水退去后最肥沃的土地上。我要亲自向他们解释,为什么要这样划分天下。”
十日后,各部落首领陆续抵达。
会场设在一片新开垦的田野旁,没有华丽的祭坛,只有九根从九州各地运来的图腾柱,按照方位矗立在平地上。柱身上雕刻着各州的标志性图腾:冀州的熊、兖州的鱼、青州的鸟、徐州的虎、扬州的蛇、荆州的鹿、豫州的牛、梁州的马、雍州的羊。
最先到达的是神农氏后裔的姜氏长老姜桓。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由两个孙子搀扶着,一下牛车就盯着雍州的羊图腾柱,脸色阴沉。
紧随其后的是黄帝嫡系后裔姬氏首领后稷,他不过三十出头,却已统领着有熊故地最大的部落。后稷年轻气盛,身后跟着二十名身披犀甲、手持铜戈的卫士——那是从蚩尤旧部传承下来的冶铁制甲技艺改良而成的装备。
“姬首领好大的阵仗。”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。
众人转头,只见一位拄着麒麟木杖的老者缓步走来。他身穿绘有八卦图案的长袍,头发用玉簪束起,虽然年迈却目光炯炯——正是伏羲氏第一百零三代后裔,风氏大巫风伯阳。
后稷连忙躬身:“风老前辈也来了。”
风伯阳摆摆手,目光扫过九根图腾柱,最终落在中央空着的石座上——那是留给禹的位置。老人眼中闪过复杂的神色,喃喃道:“划分九州……这是要终结部落时代啊。”
陆续地,燧人氏后裔火正祝融氏、少昊后裔鸟官氏、颛顼后裔高阳氏、帝喾后裔高辛氏、尧帝后裔陶唐氏、舜帝后裔有虞氏等数十个部落首领齐聚一堂。这些或老或少、或强或弱的首领们,代表着从洪荒时代延续至今的各个支脉,他们的祖先曾并肩作战,也曾兵戎相见,而今天,他们将共同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开启。
日上三竿时,禹终于出现了。
他没有骑马,也没有坐车,而是像当年治水时一样,徒步走来。伯益跟在他身后半步,手中捧着那卷九州地图。更让人惊讶的是,禹身后还跟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平民——有老农、有渔夫、有猎人,甚至还有几个脸上涂着彩泥的深山野民。
“那是谁?”姜桓皱眉问道。
风伯阳眯起眼睛看了片刻,忽然动容:“是当年治水时,在各州协助开河的平民领袖。老夫认得那个独臂老人——他叫木石,在荆州疏浚河道时被滚石砸断了手臂,却坚持领着族人干了三年。”
禹走到会场中央,没有立刻坐上石座,而是转身面向那些平民,深深一揖。
全场哗然。
“各位首领。”禹直起身,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会场,“在议事之前,我想请大家先听听这些人的声音。他们不是族长,不是巫师,不是贵族——他们是这十三年来,用双手挖开河道、用肩膀扛起石头、用生命对抗洪水的普通人。”
独臂老人木石颤巍巍走上前,看着那些衣着华贵的首领们,忽然跪了下来。
“诸位大人,”老人的声音哽咽,“小老儿的三个儿子,都死在治水的工地上。大儿子为了救被急流冲走的同伴,跳进河里再没上来;二儿子在山崩时推开旁人,自己被埋在了石头下;小儿子……小儿子是累死的,临死前手里还握着铁锹。”
会场寂静无声,只有春风吹过麦田的沙沙声。
木石抬起头,浑浊的眼里流下泪来:“可小老儿不后悔!因为禹大人说过,这水患不治,子子孙孙都要活在洪水的阴影里。如今水退了,田肥了,我的孙子们能在平原上跑跳玩耍,不用担心哪天夜里就被大水冲走——这就够了!”
另一个中年渔夫站出来:“我是兖州人,我们那儿有条河叫‘鬼哭涧’,每年雨季都要吞没几十条人命。是禹大人亲自领着我们在山壁上开凿,改了河道。去年我儿子在那里捕鱼,一网捞上来三十斤大鲤鱼!我们全村人跪在河边哭了整整一夜——那条河再也不叫‘鬼哭涧’了,我们现在叫它‘禹王渠’!”
一个接一个,平民们讲述着治水十三年的苦难与新生。有的部落首领低下头,有的红了眼眶,就连最为倨傲的后稷,也悄悄握紧了拳头。
当最后一位平民讲完,禹才缓缓走上石台,坐在那张简单的石座上。
“各位都听到了。”禹的目光扫过全场,“治水不是我一人的功绩,是天下万民用血汗换来的。今天我们划分九州,不是为了分割天下,而是为了更好地治理这片我们共同拯救的土地。”
伯益适时展开地图,高高举起。
“大家请看。”禹指着地图,“这九州的划分,依据的是山脉的走向、河流的脉络、物产的分布,而不是部落的势力范围。为什么?”
他站起身,走下石台,来到姜桓面前:“姜长老,我知道你把猎场被分割的事。但你想过没有,雍州多山,梁州多林,两地猎物习性不同。强行把猎场划在一起,只会让两州的猎人互相越界,引发冲突。如今明确界限,雍州猎人专攻山羊野鹿,梁州猎人专猎野猪虎豹,各有所长,岂不更好?”
姜桓愣住了,张了张嘴,却说不出反驳的话。
禹又走到后稷面前:“姬首领,你的卫士装备精良,令人赞叹。但你可知道,青州的铜矿、徐州的锡矿、荆州的漆树、扬州的竹子,都是制作这些甲胄兵器不可或缺的材料?如果各州封闭自守,你这身犀甲如何制成?”
后稷脸色变幻,最终躬身:“禹公教训的是。”
“我要建立的,不是一个部落联盟。”禹重新走上石台,声音如洪钟大吕,“而是一个天下共治的体系!九州各有所长,冀州产粮、兖州产盐、青州产铜、徐州制陶、扬州织锦、荆州出漆、豫州居中、梁州多木、雍州畜牧。只有九州互通有无,天下人才能丰衣足食;只有打破部落壁垒,文明才能真正进步!”
风伯阳忽然开口:“禹公之意,是要我们这些部落首领,放弃世代相传的自治权,接受九州的管辖?”
全场气氛陡然紧张。
禹看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者,忽然深深一揖:“风老,您还记得当年伏羲圣祖画八卦的初衷吗?”
风伯阳一怔。
“八卦分八方,定四时,是为了让先民掌握天地规律,更好地生存。”禹直起身,眼中闪烁着光芒,“今日我划分九州,也是如此。各部落的文化、习俗、信仰,一概保留,绝不强求一律。但在治水、防灾、通商、教化这些关乎天下民生的大事上,必须有统一的规划和调度。否则,下次洪水再来,我们还能像这次一样万众一心吗?”
他顿了顿,一字一句道:“我不是要消灭部落,我是要让所有部落,在更大的框架下更好地活下去。”
长久的沉默。
忽然,姜桓颤巍巍站起身,走到会场中央,面向禹跪了下来。
“神农氏后裔姜氏,”老人声音嘶哑却坚定,“愿遵从九州划分,奉禹公为天下共主!”
像是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,一个接一个的首领起身下跪。
“黄帝后裔姬氏,愿奉禹公为天下共主!”
“伏羲氏后裔风氏,愿奉禹公为天下共主!”
“燧人氏后裔祝融氏……”
“少昊后裔鸟官氏……”
“颛顼后裔高阳氏……”
最终,连最年长、最保守的风伯阳也缓缓起身,却没有立刻下跪。他走到禹面前,从怀中取出一块古朴的龟甲。
“这是伏羲圣祖传下的八卦原甲,”风伯阳将龟甲双手奉上,“一千三百年来,风氏世代守护。今日,老夫将它交给禹公——不是因为你划分了九州,而是因为你让老夫看到了,什么才是真正的‘天下为公’。”
禹郑重接过龟甲,那上面古老的裂纹仿佛在诉说着洪荒以来的所有智慧。
“谢风老。”禹的声音有些哽咽,“禹必不负此甲,不负天下。”
禅让大典定在三个月后的夏至日。
这期间,伯益忙得脚不沾地。他要协调各州贡品的运送,要安排大典的仪程,还要处理那些细碎却棘手的问题:雍州和梁州因为新划边界处的两处泉眼归属起了争执;青州铜矿的矿工不满劳作条件,集体罢工;扬州进贡的丝绸在运输途中被山贼劫掠……
夜深人静时,伯益常常独自坐在营帐中,对着烛火发呆。
“伯益大人还没休息?”帐帘被掀开,一个温和的声音传来。
伯益抬头,看见皋陶的孙子皋禹——如今已是部落联盟的首席法官——端着两碗粟米粥走了进来。这年轻人继承了祖父的刚正不阿,却多了几分圆融智慧。
“是皋禹啊。”伯益揉了揉眉心,“坐吧。”
皋禹放下粥碗,在伯益对面坐下。烛光映照着他年轻却沉稳的脸:“大人是在为大典的事烦心,还是……在为禅让之后的事烦心?”
伯益的手顿住了。
良久,他苦笑道:“你都看出来了。”
“天下人都看出来了。”皋禹轻声道,“舜帝年老体衰,禅让是迟早的事。而禹公治水功高盖世,威望遍及九州,这共主之位非他莫属。只是……”
“只是按照禅让制的传统,”伯益接过话头,声音低沉,“禹公应该选定继承人,而那个人,很可能就是我。”
皋禹沉默了片刻:“大人不愿意?”
“不是不愿意。”伯益摇摇头,眼中闪过复杂的神色,“只是我常想,我真的配吗?这十三年来,我跟随禹公治水,亲眼见证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赢得民心的。他三过家门而不入,他脚上的老茧比牛皮还厚,他和民夫一起吃糙米、睡草棚……这样的功绩,这样的德行,古往今来能有几人?而我伯益,不过是帮他处理些文书、协调些杂务罢了。”
“但禹公信任你。”皋禹认真地说,“这十三年来,他所有的决策几乎都会与你商议。各州首领、各部落长老,谁不知道伯益大人是禹公最得力的臂膀?更重要的是,大人您继承了皋陶爷爷的法治精神,又精通各州物产民情,是最懂得如何治理这个新天下的人。”
伯益端起粥碗,却没有喝:“皋禹,你说实话——如果我继位,天下人会服吗?”
这次,皋禹沉默了更久。
“会有人服的。”最终,他谨慎地选择着措辞,“各州首领中,至少有一半敬重您的才能。但也会有人不服,尤其是……那些心向启公子的人。”
启。
这个名字让伯益的手微微一颤。
启是禹的独子,今年不过二十五岁,却已在治水后期崭露头角。他继承了禹的果敢,却又多了几分锐气——或者说,是野心。在最后两年的治水工程中,启常常独立带领一支队伍,开山劈石,雷厉风行。他善待士卒,赏罚分明,却也手段强硬,对那些拖延工期的部落毫不留情。
更重要的是,启身上流淌着黄帝、颛顼、鲧、禹四代英雄的血脉。在那些重视血统的古老部落看来,启才是“天然”的继承人。
“启公子年轻有为,”皋禹继续说道,“治水后期,他在梁州疏通‘鬼见愁’峡谷的事迹,已经传遍九州。百姓都说,虎父无犬子。而且他毕竟是禹公的亲生骨肉,那些感念禹公恩德的部落,自然会爱屋及乌。”
伯益放下粥碗,长叹一声:“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。禅让制的精髓,在于传贤不传子。如果因为禹公的功绩,就让他的儿子继位,那禅让制就名存实亡了。可是……”
他苦笑:“可是如果让我这个‘外人’继位,启公子会甘心吗?那些支持启的势力会答应吗?天下刚刚从洪水中复苏,再也经不起一场内部争斗了。”
皋禹看着伯益疲惫的脸,忽然问道:“那大人自己的心意呢?您真的不想成为天下共主吗?”
伯益愣住了。
烛火噼啪作响,在帐壁上投下摇曳的影子。良久,伯益才缓缓开口,声音轻得像是在自言自语:
“小时候,我祖父常对我说,伯益啊,你要记住,权力不是荣耀,是责任。他给我讲尧帝禅让给舜帝的故事,讲舜帝如何以德服人、以孝感天。那时我就想,如果有一天我也能被这样信任、被这样托付,该是多么荣幸的事。”
他抬起头,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:“我想,我是想的。我想继续禹公未竟的事业,想让九州真正融为一体,想让天下人都过上好日子。但是……如果这个位置需要用分裂和争斗来换取,我宁愿不要。”
皋禹站起身,深深一揖:“无论大人作何决定,皋禹都会站在您这一边。”
伯益看着这个年轻人,忽然笑了:“你比你祖父会说话多了。皋陶大人当年可是直接指着尧帝的鼻子批评他任人唯亲的。”
“时代不同了。”皋禹也笑了,“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——比如对正义的追求,对天下的责任。”
帐外传来更鼓声,已是子夜。
“去休息吧。”伯益说,“明天还要接待从扬州来的贡使。”
皋禹躬身退出。伯益独自坐在帐中,看着跳动的烛火,忽然从怀中取出一卷竹简——那是禹昨天交给他的,上面记录着各州的人口、物产、山川形胜。
“治理天下……”伯益轻抚竹简,喃喃自语,“真的比治理洪水容易吗?”
夏至日终于到来。
禅让大典在冀州平原新筑的祭坛举行。这座祭坛高九丈,象征九州;四面各有九级台阶,象征九九归一。坛顶平整如砥,中央矗立着一尊三足大鼎——那是用九州进贡的铜锡合铸而成,鼎身上浮雕着治水十三年的重要场景:开凿龙门、疏导淮泗、劈开三峡、划定九州……
旭日东升时,各州首领、部落长老、平民代表已齐聚坛下。人群从祭坛一直延伸到远处的田野,黑压压望不到边。这是自涿鹿之战以来,华夏大地上最盛大的一次聚会。
吉时将至,舜帝在两名侍从的搀扶下登上祭坛。
这位年过八旬的老者,已经须发皆白,步履蹒跚。但他的眼睛依然清澈,那是历经沧桑后沉淀下的智慧之光。舜帝穿着简朴的麻布衣袍,头戴荆冠——那是他年轻时在历山耕种时常戴的帽子。
坛下鸦雀无声。
舜帝走到祭坛中央,面向东方升起的太阳,缓缓跪下。全场数万人随之跪倒,动作如潮水般层层推开。
“皇天在上,后土在下。”舜帝的声音苍老却洪亮,“自伏羲画卦、神农尝草、黄帝立制以来,天下共主之位,皆传于贤德。今日,舜年老力衰,已不堪负天下之重。察天下有德者,莫过于禹。”
他转过身,看向坛下:“禹,上前来。”
禹从人群中走出。他今日穿着涂山氏亲手缝制的黑色礼服,上面用金线绣着龙纹——那是黄帝部落的图腾。但出人意料的是,禹的脚上依然穿着那双磨破了边的草鞋。
一步,一步,禹缓缓登上祭坛。他的脚步很稳,每一步都踏得坚实有力。当他终于站在舜帝面前时,全场屏住了呼吸。
舜帝从怀中取出一块玄玉——那是尧帝禅让时交给他的信物,据说最初来自黄帝。
“禹,”舜帝双手捧玉,声音颤抖,“你治水十三年,劳身焦思,胼手胝足,终于平定水患,拯救苍生。你划分九州,通有无,利民生,奠定天下长治久安之基。你的功德,上达天听,下及幽冥。今日,我将这天下共主之位传于你,望你继续以德治国,以仁爱民,不负天意,不负人心。”
禹没有立刻接玉。
他后退一步,撩起衣袍,向着舜帝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。每一次叩首,额头都重重磕在祭坛的青石板上,发出沉闷的响声。
三跪九叩毕,禹才直起身,却没有看那块玄玉,而是看向坛下的万民。
“舜帝,”禹的声音响彻天地,“禹本愚钝,受命治水,不过是尽人子之本分。今日之天下,非禹一人之功,是万民血汗所铸。这共主之位,禹不敢轻易接受。”
全场哗然。
舜帝也怔住了:“禹,你这是……”
“请舜帝、请天下人听我一言。”禹转向坛下,目光扫过那一张张面孔,“这十三年来,我走遍九州,看到洪水退去后,百姓依然困苦。冀州有田无种,兖州有盐无粮,青州有铜无衣,徐州有陶无器……九州各自为政,物产不能流通,技艺不能传播,这样下去,即使没有洪水,百姓也难以富足。”
他深吸一口气:“所以,在接下这共主之位前,我要向天下人立下誓言:第一,设立九州牧,每州选贤能者任之,负责协调本州事务,但必须遵从天下共主号令;第二,开辟九州通衢,修整道路,疏通河道,让货物流通无阻;第三,统一度量衡,让九州交易有准,避免欺诈;第四,设立常平仓,丰年储粮,荒年放赈,以防饥馑;第五……”
禹一连说了九条誓言,条条关乎民生,句句切中时弊。坛下的百姓听得如痴如醉,不少老人已经开始抹眼泪。
“最后,”禹的声音忽然低沉下来,“我要立下禅让之誓。自我禹开始,天下共主之位,必传于贤能,而非血亲。今日在此,我当众选定继承人——”
全场死寂。
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伯益。这位跟随禹十三年的助手站在人群最前方,身体微微颤抖。
然而,禹却说道:“我的继承人是——伯益!”
伯益猛地抬头,眼中闪过震惊、感动、惶恐……万般情绪。
“但是,”禹话锋一转,“禅让之制,精髓在于‘选贤’。伯益今日贤能,故我选他。若他日有更贤能者,伯益亦当禅让。如此代代相传,天下永得明主,百姓永享太平!”
他这才转过身,从舜帝手中接过玄玉,高举过头顶。
阳光照射在玄玉上,折射出温润的光芒。禹面向东方,朗声宣告:
“自今日起,我禹,承天受命,继舜为天下共主!必以九州为念,以万民为心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!皇天后土,实所共鉴!”
“万岁!万岁!万岁!”
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席卷平原,震得祭坛都在微微颤动。人们挥舞着手臂,热泪盈眶,有人甚至激动得昏厥过去。
舜帝老泪纵横,握住禹的手:“天下交给你,我放心了。”
禅让大典在持续一整天的祭祀和欢庆中结束。当晚,各州首领齐聚禹的临时行宫——那不过是几座稍大的营帐罢了。
禹坐在主位,伯益坐在他身侧。下面分两列坐着九州牧的候选人,以及各主要部落的首领。
“今日之誓,各位都听到了。”禹开门见山,“九州牧的人选,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”
众人面面相觑。最终还是风伯阳先开口:“冀州为天下之中,又是新都所在,这冀州牧的人选最为关键。老夫推荐皋禹——他年轻有为,又精通律法,且是皋陶大人嫡孙,德才兼备。”
皋禹连忙起身:“小子才疏学浅,不敢当此重任。”
“我看可以。”姜桓点头,“皋陶大人一生公正,天下敬仰。皋禹继承家学,又在治水中历练多年,确实合适。”
其他首领也纷纷附和。
禹看向伯益:“你觉得呢?”
伯益沉吟道:“皋禹确实是最佳人选。不过我建议,九州牧中,至少要有三位来自平民——木石老人虽然年迈,但德高望重,可以任兖州牧;那个在青州组织矿工治水的工头石坚,可以任青州牧;还有……”
他一一列举,每提到一个名字,就简要说明其功绩和德行。禹听得频频点头,各首领虽然有些疑虑,但想到白天禹的誓言,也不好反对。
最终,九州牧的人选确定:四位来自古老部落,三位来自平民领袖,两位来自归附的九黎后裔部落——这体现了禹“天下为公,唯才是举”的理念。
议事一直持续到深夜。当众人散去,营帐中只剩下禹和伯益时,伯益忽然跪了下来。
“禹公,”伯益声音哽咽,“伯益……何德何能,受此重托?”
禹扶起他,目光温和:“伯益,这十三年来,你不仅是我的助手,更是我的知己。你记得吗?在疏浚淮河时,我高烧三日,是你日夜守候,代我指挥;在划分九州时,是你走遍每一处边界,实地勘察;今天这九州牧的人选,你也早已心中有数……这样的才能,这样的德行,不传给你,传给谁?”
“可是启公子……”伯益欲言又止。
禹的神情黯淡下来。他走到帐边,掀开帘子,看着夜空中的星辰。良久,才缓缓道:“启是我的儿子,我了解他。他有才干,有魄力,但……太过锐利,少了仁厚。治天下不是治水,不能只靠雷霆手段。而且,”
他转过身,眼中闪过痛苦之色:“如果我传位给启,禅让制就真的名存实亡了。后世子孙会想:连禹这样的大贤都传子,我们凭什么传贤?如此一代传一代,终有一天,会传到昏庸暴戾之徒手中,那时天下百姓该怎么办?”
伯益震撼地看着禹。他没想到,禹想得如此深远。
“所以,我必须立你这个榜样。”禹握住伯益的手,“我要让天下人看到,我禹可以传位给毫无血缘关系的贤能,后世共主也应当如此。只有这样,禅让制才能真正延续,天下才能永得明主。”
“可是启公子会理解吗?”伯益担忧地问。
禹沉默了。夜风吹动帐帘,带来远处篝火的噼啪声和隐约的欢歌。
“启那边,我会去说。”最终,禹轻声道,“你只需记住:无论将来发生什么,都要以天下苍生为念。如果有一天,启真的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,你就该学尧舜,主动禅让。但如果他只是为了权力而争……伯益,该坚持的时候,一定要坚持。”
伯益重重点头,眼中含泪:“伯益谨记。”
那一夜,两个并肩作战十三年的老友,在营帐中谈了整整一夜。他们回忆治水路上的艰辛,畅想九州未来的图景,也担忧着暗流涌动的变局。
而当他们谈话时,在另一座营帐中,启正对着一盏孤灯,面色阴沉。
“公子,”一个心腹低声道,“今日大典上,禹公当众宣布传位给伯益,这……这置您于何地啊?”
启没有说话,只是用手指轻敲着桌案。烛光在他年轻的脸上跳动,勾勒出坚硬的轮廓。
“伯益确实有才能,”另一个幕僚小心翼翼地说,“而且跟随禹公多年,功劳苦劳都不小。按照禅让制的传统,传贤不传子,禹公的选择也合乎古礼……”
“古礼?”启终于开口,声音冰冷,“神农传炎帝,黄帝传颛顼,颛顼传帝喾——哪个不是血亲相传?尧舜禅让,那是特例!如今父亲功高盖世,救天下于洪水,这共主之位本就该由我夏后氏世代相传才对!”
他猛地站起身,在帐中踱步:“你们知道各部落现在怎么议论吗?他们说,启公子虽然能干,终究比不上伯益老成持重;他们说,禹公大公无私,是真正的圣人;他们说……说我启,不过是倚仗父亲威名的纨绔子弟!”
“公子息怒。”心腹连忙劝道,“那些都是无知小民的胡言乱语。治水后期,公子独自疏通‘鬼见愁’峡谷,威震梁州,这是有目共睹的功绩!各部落中,支持公子的大有人在,尤其是那些看重血统的古老部落……”
启停下脚步,眼中闪过锐利的光:“都有哪些部落?”
心腹凑近,低声道:“黄帝嫡系的姬氏,已经暗中派人接触过;神农氏的姜氏,虽然白天表态支持禹公,但姜桓长老私下对传位伯益颇有微词;还有颛顼后裔的高阳氏、帝喾后裔的高辛氏……这些圣王后裔,谁不希望看到共主之位在圣王血脉中传承?伯益算什么?他的祖先不过是尧帝时期的一个小部落首领罢了!”
启的嘴角勾起一丝冷笑:“继续联络这些部落。记住,要隐秘。”
“那伯益那边……”
“伯益?”启坐回座位,把玩着手中的玉杯,“他是个聪明人。如果他能识时务,主动让贤,我继位后不会亏待他。但如果他执迷不悟……”
他没有说下去,但眼中闪过的寒光,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打了个冷战。
帐外,夏至的夜空繁星点点。一颗流星划过天际,拖出长长的光尾,转瞬即逝。
新的时代开始了,但通往这个时代的道路,注定不会平坦。
禅让之后的三年,是九州大地快速复苏的三年。
在禹的推动下,九州通衢开始修建。以冀州为中心,八条大道向四面八方延伸:东通青徐,西连雍梁,南接荆扬,北达兖州。每三十里设驿站,每百里设货栈,商旅往来,络绎不绝。
伯益作为继承人,实际上承担了大部分政务。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处理各州送来的文书,接见各部落使者,巡视新开垦的农田,视察正在修建的水利工程……他的才能在这三年里得到充分展现,政令畅通,民生改善,各州牧对他心服口服。
但暗流,从未停止涌动。
第四年春天,禹决定巡视九州。这是他继位后第一次全面巡视,目的有三:一是实地考察各州治理情况;二是调解一些积压的纠纷;三是向天下展示新朝的气象。
伯益留守冀州,代行共主之职。而启,作为禹的儿子,自然陪同巡视。
巡视队伍从冀州出发,第一站是东方的青州。
青州多铜矿,治水后期,这里的矿工在禹的指挥下,用开采的铜矿石冶炼青铜,制作工具,大大提高了治水效率。如今洪水退去,青铜冶炼技术被用于制作农具、礼器和兵器,青州因此成为九州中最富庶的州之一。
青州牧石坚——就是当年那个组织矿工治水的工头——率领百姓在州界迎接。当禹的车驾出现在视野中时,上万百姓跪倒在道路两侧,高呼万岁。
“都起来吧。”禹走下马车,亲手扶起前排的老人,“我不是来受礼的,是来看望大家的。”
他走进百姓中间,询问收成如何,赋税重不重,孩子有没有上学……这些问题朴实而具体,却让青州百姓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一个老矿工挤到前面,颤巍巍地捧出一把青铜镰刀:
“禹王,这是小老儿用第一炉青铜打的镰刀,锋利着呢!去年收麦子,一亩地能省半天工!小老儿想把这把镰刀献给禹王,愿禹王像这镰刀一样,为天下割除苦难!”
禹郑重接过镰刀,抚摸那光滑的刃口,眼中也湿润了:“好,好。这把镰刀我收下了。它不是给我的,是给天下农民的。我要让各州的工匠都来青州学习这青铜冶炼之术,让九州百姓都用上这样的好农具!”
人群爆发出欢呼声。
启站在父亲身后,看着这一幕,心中五味杂陈。他羡慕父亲如此轻易就能赢得民心,也有些不屑——觉得这些收买人心的手段太过刻意。但他不得不承认,父亲确实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,那是十几年与民同甘共苦磨炼出来的气质。
当晚,青州牧府设宴招待。
宴席上,石坚汇报了青州的情况:铜矿产量比三年前翻了一番;新开垦的农田达到五万亩;建立了三所乡学,教授孩童识字算术;还按照禹的要求,设立了常平仓,储存了足够全州百姓吃一年的粮食……
“做得好。”禹频频点头,“不过我有两个问题。”
“禹王请讲。”
“第一,矿工的工作条件改善了吗?我听说还有矿洞塌方的事故发生。”
石坚连忙道:“已经改善了。现在每个矿洞都有木架支撑,矿工每天只工作四个时辰,每十天休息一天。去年只发生了一次小塌方,伤了三个人,都已经妥善医治和抚恤。”
“第二,青州的青铜技术,传授给其他州了吗?”
“这……”石坚犹豫了一下,“按照您的命令,我们已经派人去徐州、豫州传授技术。但有些工匠……不太愿意把独门手艺外传。”
禹皱眉:“这不行。技术不是一州一地的私产,是全天下的财富。这样,你从各州选拔聪明伶俐的年轻人,集中到青州学习,学成后回本州传授。学得好的人,给予重奖。那些保守的工匠,也要耐心开导——告诉他们,技术传播出去,别州会用粮食、布匹来交换,大家都能得利。”
“是,禹王英明。”
宴席进行到一半,启忽然开口:“石州牧,我听说青州的青铜兵器制作精良,不知能否让我见识见识?”
石坚一愣,看向禹。
禹微微点头:“启对兵器制造颇有兴趣,让他看看吧。”
石坚这才吩咐手下取来几件青铜兵器:戈、矛、剑、戟,在烛光下闪着幽冷的光芒。
启拿起一把剑,轻轻一弹,发出清脆的嗡鸣。他走到院中,舞了几个剑花,动作矫健凌厉,引来一片喝彩。
“好剑!”启赞叹,“比石刀石矛锋利十倍不止。这样的兵器,应该装备九州军队。”
石坚笑道:“公子说的是。不过禹王有令,青铜优先用于制作农具,兵器只做少量,主要给各州卫队使用。”
启的脸色微微一沉,但很快恢复笑容:“父亲考虑得周到。农具关乎民生,确实更重要。”
但他心中,却涌起一股不满。在启看来,父亲太过仁慈,甚至有些迂腐。如今九州初定,看似太平,实则暗流涌动——那些古老的部落,那些归附的九黎后裔,那些新崛起的州牧……谁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?没有强大的武力震慑,单靠仁德,能维持多久?
宴席结束后,启回到住处,召来随行的谋士。
“你们看到了吗?”启冷声道,“父亲对兵器的态度。他以为靠仁德就能治天下,真是天真。”
谋士低声道:“公子,禹王确实过于重文轻武了。如今各州都有卫队,但人数不过数百,兵器也多是石制、骨制。如果真有人起兵造反,恐怕难以镇压。”
“青州的青铜兵器制作技术,”启眼中闪过精光,“我们必须掌握。不仅是青州,徐州制陶、扬州织锦、荆州漆器……这些关键技术,都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。”
“公子的意思是……”
“培养我们的人。”启走到窗边,看着夜空,“在各州的关键位置,安插我们的人。表面上遵从父亲的政令,暗地里积蓄力量。等到时机成熟……”
他没有说下去,但谋士已经明白了。
那一夜,启房中的灯火亮到很晚。
而与此同时,在另一个房间,禹也没有睡。他坐在案前,翻阅着石坚送来的青州详细报告,眉头紧锁。
门被轻轻推开,一个老侍从端着药碗进来:“禹王,该喝药了。”
禹抬起头,揉了揉太阳穴:“放下吧。”
老侍从担忧地看着他:“禹王,您这咳嗽的毛病越来越重了,巡视路上又这么劳累……要不,后面的州就别去了,回冀州休养吧。”
禹摇摇头:“不行。这次巡视很重要,我必须亲自看看各州的真实情况。伯益虽然能干,但有些事,只有亲眼所见才能明白。”
他喝下苦药,又问:“启今天在宴席上的表现,你怎么看?”
老侍从犹豫了一下:“启公子……似乎对兵器很感兴趣。”
“是啊。”禹叹了口气,“这孩子,太过尚武。治天下不能只靠武力,要以德服人,以理服人。可他不懂,或者说,不愿意懂。”
“启公子还年轻,以后会明白的。”
“就怕他等不到明白的时候。”禹望向窗外,眼中满是忧虑,“伯益和启……我总担心,我死之后,他们会起冲突。伯益德才兼备,但性格太过温和;启果敢强硬,却少了仁厚。如果他们能互补该多好,可惜……”
他摇摇头,不再说下去。
巡视继续进行。从青州到徐州,从徐州到扬州,从扬州到荆州……禹每到一个州,都深入民间,了解百姓疾苦,解决实际问题。他的威望与日俱增,各州百姓甚至开始为他立生祠,早晚祭拜。
但启心中的不满,也在与日俱增。
在荆州时,发生了一件小事,却让父子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。
那天,禹视察荆州的漆器作坊。漆器是荆州的特产,用来制作食器、礼器,精美绝伦。作坊的主人是个老匠人,他献给禹一套漆器酒具,上面用金粉绘着治水的场景。
“禹王,”老匠人跪在地上,“这套酒具,小老儿做了整整一年。愿禹王用它饮酒时,能想起我们荆州百姓对您的感恩。”
禹接过酒具,却皱起了眉头:“这上面的金粉,是从哪里来的?”
“是……是从金矿开采的。”老匠人有些惶恐。
“荆州有金矿?”禹转向荆州牧,“我怎么不知道?”
荆州牧连忙解释:“是一座小金矿,产量很小,以前一直由当地部落私下开采。我们设立州牧后,将其收归公有,但觉得这事不大,就没上报……”
“糊涂!”禹罕见地动了怒,“金矿再小也是国家资源,岂能隐瞒不报?而且这金粉用来装饰漆器,太过奢侈。如今百姓刚刚温饱,怎能如此浪费?”
他转向老匠人,语气缓和了些:“老师傅的手艺确实精湛,这漆器我收下了。但这金粉,请你刮下来,熔成金块,充入州库。以后荆州的黄金,优先用于制作农具的模具、测量工具,或者作为货币储备,不能用于装饰玩乐之物。”
老匠人脸涨得通红,连连称是。
在场的地方官员也都低下头,不敢说话。
只有启,忍不住开口:“父亲,一套酒具而已,何必如此苛责?这位老师傅也是一片心意。”
禹看向儿子,目光严厉:“启,你可知这一套酒具上的金粉,能打多少把锄头?能救多少饥民?为君者,一言一行都要为天下表率。我今天收下这金漆酒具,明天各州就会争相进献珍奇玩物,后天官员就会搜刮民脂民膏来讨好上级——如此上行下效,不出三年,奢侈之风就会席卷九州,到时再想遏制就难了!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没有可是!”禹斩钉截铁,“勤俭节约,是治国之本。尧帝住茅屋、喝菜汤,舜帝穿粗衣、耕历山,他们不是不能享受,是不敢享受!因为一旦君王开始追求享受,离失去民心就不远了!”
启张了张嘴,最终还是低下头:“父亲教训的是。”
但当他走出作坊时,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。
“公子,”心腹跟上来,低声道,“禹王这也太过……一套酒具而已,何必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您下不来台?”
启咬着牙,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:“他觉得我不配当这个共主。他觉得只有伯益那样的‘圣人’,才配。”
那一刻,启心中最后一丝犹豫也消失了。
巡视九州用了整整一年时间。当队伍终于回到冀州时,已是又一年的春天。
伯益率领百官在城外迎接。当他看到禹从马车上下来时,心中一惊——仅仅一年,禹苍老了许多,腰背佝偻了,咳嗽也更频繁了,只有那双眼睛,依然炯炯有神。
“禹公!”伯益上前搀扶。
禹握住他的手,微笑道:“伯益,这一年辛苦你了。冀州治理得很好,我刚才一路看来,农田连片,市井繁荣,百姓脸上都有笑容——这都是你的功劳。”
“伯益只是遵照禹公的政令行事。”伯益谦逊地说,但心中涌起暖流。
当晚,禹召集伯益、启,以及几位重臣,听取这一年的政务汇报。
伯益的汇报条理清晰,数据详实:冀州新开垦农田十二万亩;修建大型粮仓八座,储粮足够全州三年之用;建立乡学二十所,孩童入学率达到四成;调解部落纠纷四十七起,全部妥善解决……
禹听得频频点头:“好,很好。伯益,你有宰相之才。”
这句话让启的脸色又阴沉了几分。
轮到启汇报巡视情况时,他着重讲了各州的军事情况:青州的青铜兵器产量、徐州的弓箭制作、荆州的战车制造……还建议扩大各州卫队规模,加强训练。
“父亲,”启最后说,“如今九州看似太平,实则隐患重重。各州新设,权威未固;部落旧俗,根深蒂固;九黎后裔,未必真心归附。我们应当未雨绸缪,建立一支强大的中央军队,驻扎冀州,随时应对不测。”
禹沉吟片刻,看向伯益:“你觉得呢?”
伯益谨慎地说:“启公子的担忧不无道理。但如今民生刚有起色,大规模扩军必然增加赋税,加重百姓负担。而且中央军队驻扎冀州,各州难免猜疑,反而不利于团结。我以为,当前还是应以安抚民生、发展生产为主,军事上只需维持各州卫队的基本防御即可。”
“伯益大人太过书生气了。”启忍不住反驳,“没有武力保障的和平,不过是空中楼阁。当年黄帝若无强大军力,怎能击败蚩尤、统一各部?父亲治水靠的是万民齐心,但治国不能只靠人心——人心是会变的!”
“启!”禹喝道,“怎么说话呢?”
伯益摆摆手:“禹公息怒,启公子说得也有道理。只是……军事与民生,如何平衡,确实需要慎重考虑。”
那场会议不欢而散。
会后,禹将启单独留下。
“启,你今天太失礼了。”禹疲惫地靠在榻上,“伯益是你的长辈,也是我选定的继承人,你应该尊重他。”
启跪在地上,却不低头:“父亲,我只是说出心中所想。伯益大人确实德高望重,但他太过温和,甚至有些软弱。如今这天下,表面风平浪静,底下暗流涌动,没有铁腕手段,如何镇得住?”
“你以为治国就是镇压吗?”禹失望地看着儿子,“黄帝击败蚩尤,靠的不仅是武力,更是仁义。他接纳九黎部众,传承他们的技艺,这才有华夏族的大融合。如果只靠武力镇压,今天镇压这个,明天镇压那个,天下永无宁日!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没有可是。”禹闭上眼睛,“启,我最后说一次:伯益是我的继承人,这是不会改变的决定。你要做的,是好好辅佐他,学习他的长处,弥补他的不足。将来他继位后,你就是他最得力的臂膀——这样不好吗?”
启没有说话,只是拳头在袖中握得死紧。
那一刻,他心中最后一点父子之情,也凉了。
又两年过去了。
禹的身体每况愈下。咳嗽越来越重,有时甚至会咳出血来。太医说,这是长年劳累、风寒入骨所致,需要静养。但禹不听,依然每天处理政务,接见使者,巡视农田。
第五年秋天,禹终于倒下了。
那是在视察黄河新堤坝时,一阵秋风吹来,禹剧烈地咳嗽起来,咳着咳着,忽然喷出一口鲜血,昏倒在地。
众人慌忙将他抬回宫中。伯益、启、各州牧、各部落首领,闻讯纷纷赶来冀州。
太医诊断后,摇头叹息:“禹王积劳成疾,脏腑皆损,恐怕……恐怕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”
消息传出,九州震动。百姓自发在各地祭祀祈福,祈求上天保佑禹王康复。各州牧联名上书,请求禹王静养,政务由伯益暂代。
伯益日夜守在禹的病榻前,亲自煎药喂药,眼窝深陷,憔悴不堪。
启也守在父亲身边,但他的眼中,除了担忧,还有别的什么东西。
一天深夜,禹从昏睡中醒来,看到伯益趴在榻边睡着了。他艰难地伸出手,轻拍伯益的肩膀。
伯益惊醒:“禹公,您醒了?要喝水吗?”
禹摇摇头,示意他靠近些:“伯益,我的时间不多了。”
“禹公别这么说,您会好起来的……”
“我自己知道。”禹苦笑,“伯益,我走之后,这天下就交给你了。你记住我当初的话:以德治国,以仁爱民。但也别忘了,该强硬的时候要强硬——对那些心怀不轨的人,不能一味仁慈。”
伯益含泪点头:“伯益谨记。”
“还有启……”禹的眼神黯淡下来,“这孩子,心气太高,野心太大。我担心他会对你不利。如果……如果他真的起兵夺位,你不要手软。为了天下太平,该镇压就要镇压。但,尽量留他性命——他毕竟是我的儿子,也是个人才,流放边疆,让他反省就好。”
伯益泣不成声:“禹公,不会的,启公子不会那样的……”
禹握住他的手,用力地握了握:“但愿吧。”
他顿了顿,又说:“我死之后,不要厚葬。就在黄河边,找一块普通土地,挖七尺深,用陶棺下葬,不起坟冢,不立碑石。我治水一生,最后也要守着这条河。还有,我那些治水时的工具——石斧、铁锹、测量绳——都随葬。我生时用它们治水,死后也要用它们,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开山辟河。”
伯益已经哭得说不出话。
几天后,禹的精神突然好了些,甚至能坐起来喝粥了。大家都以为出现了奇迹,但太医私下对伯益说:“这是回光返照,禹王……就在这几天了。”
果然,三天后的清晨,禹将伯益、启、皋禹、以及几位重臣召到榻前。
他穿着整洁的麻布衣袍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靠在榻上,虽然面色苍白,眼神却依然清明。
“都来了。”禹微笑着,“坐吧,我有话说。”
众人依次坐下,心中都沉甸甸的。
“我的时间到了。”禹平静地说,“今天叫你们来,是要交代后事。伯益。”
“在。”
“你跟我最久,最懂我的心思。我死之后,你继位为天下共主。我已经写好了禅让诏书,盖了玄玉印,就在那个漆盒里。”他指了指案上的一个黑色漆盒。
伯益跪地叩首,泪流满面。
“启。”
启上前跪下:“父亲。”
禹看着儿子,眼中满是复杂的情感:“启,你是我唯一的儿子,我怎么会不爱你?但爱之深,责之切。你太过锐利,需要磨砺。我让伯益继位,不是不信任你,是要给你时间成长。你要好好辅佐伯益,学习他的德行和智慧。等时机成熟,伯益自然会传位给你——我向他交代过的。”
启浑身一震,猛地抬头看向伯益。
伯益也愣住了——禹从未对他说过这样的话。
但看着禹恳求的眼神,伯益瞬间明白了。禹是在用最后的力气,为他和启之间铺一条和解的路。
“是,父亲。”启低下头,声音哽咽,“儿子明白了。”
“皋禹。”禹又唤道。
“禹王。”皋禹跪前一步。
“你祖父皋陶,一生公正严明,是我最敬重的人之一。你要继承他的遗志,辅佐伯益,执掌刑律,维护天下正义。”
“皋禹遵命。”
“还有各位州牧、各位首领……”禹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,“天下初定,百废待兴。我走之后,希望你们能团结一心,共同辅佐伯益,把九州治理得更好。记住,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,不是一姓一族的天下。只要心中装着百姓,做什么决定都不会错。”
众人齐齐跪倒:“谨遵禹王教诲!”
禹满意地点点头,靠在榻上,闭上了眼睛。他的呼吸渐渐微弱,嘴角却带着一丝微笑。
伯益扑到榻前,握住禹的手:“禹公!禹公!”
禹的眼睛睁开一条缝,看着伯益,用最后的力气说:“天下……交给你了……”
手,垂落。
公元前2076年秋,大禹,这位治水十三载、划定九州、开创夏朝的伟大君主,在冀州宫中与世长辞,享年五十八岁。
消息传出,九州同悲。从冀州到扬州,从雍州到荆州,百姓自发披麻戴孝,祭奠这位拯救天下于洪水的英雄。黄河两岸,哭声震天,据说连河水都为之呜咽。
按照禹的遗愿,伯益主持了简朴的葬礼。没有华丽的陵墓,只有黄河边一座不起眼的土丘;没有丰厚的陪葬,只有那些磨秃了的治水工具。但送葬的队伍绵延百里,各州百姓扶老携幼,前来送禹王最后一程。
葬礼上,伯益宣读禹的遗诏,正式继位为天下共主。各州牧、各部落首领当众宣誓效忠,仪式庄严肃穆。
但敏锐的人已经察觉到,暗流正在涌动。
葬礼结束后第三天,启以“守孝”为由,离开了冀州,回到了自己的封地阳城。
伯益本想挽留,但皋禹私下劝道:“启公子此时离开,未必是坏事。他在冀州,各方势力蠢蠢欲动,反而不利于稳定。让他回封地冷静一段时间也好。”
伯益想了想,同意了。他还特意派人给启送去慰问,并承诺:三年守孝期满后,一定重用于他。
启在阳城恭敬地回信致谢,表示一定谨守孝道,不忘父亲教诲。
然而在阳城的府邸中,一场密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。
“公子,”心腹谋士低声汇报,“姬氏、姜氏、高阳氏、高辛氏的代表都已经秘密抵达,安排在别院中。”
启站在窗前,看着庭院中飘落的秋叶,面无表情:“伯益那边有什么动静?”
“伯益公继位后,第一道政令是减免各州三年赋税;第二道是继续推行九州通衢计划;第三道是扩大乡学规模……都是收买人心的举措。各州牧对他颇为支持,尤其是那些平民出身的州牧。”
“平民……”启冷笑,“他倒是会拉拢底层。那些古老部落呢?什么反应?”
“表面恭顺,实则不满。姜桓长老私下抱怨,说伯益出身低微,不配统领圣王后裔。后稷更是直言,天下共主之位,应该在有德者中选拔没错,但有德者未必不能出自圣王血脉——这明显是在为公子造势。”
启转过身,眼中闪着锐利的光:“联络所有对伯益不满的势力。记住,要隐秘,不要留下把柄。”
“是。还有……九黎后裔那边,也有人接触我们。他们虽然归附多年,但一直被视为异族,待遇不公。如果我们承诺平等相待,他们愿意支持公子。”
启沉思片刻:“可以答应。但记住,承诺归承诺,等事成之后……再说。”
谋士心领神会地退下。
启独自站在房中,从怀中取出一块玉佩——那是禹生前常佩戴的,上面刻着一个“夏”字。禹临终前将这块玉佩给了启,说:“这是你祖父鲧留下的,上面这个‘夏’字,是我们部族的称号。你留着,做个念想。”
“夏……”启轻抚玉佩,喃喃自语,“父亲,您把这个字留给我,是不是在暗示什么?夏后氏,夏后氏……既然以‘夏’为号,这天下,难道不该由夏后氏来掌管吗?”
他握紧玉佩,眼中燃起熊熊的火焰。
那一夜,阳城的灯火彻夜未熄。
而在冀州,伯益也夜不能寐。
他站在禹曾经站过的观星台上,仰望满天繁星。秋风萧瑟,吹动他的衣袍。
“伯益公,夜深了,回去休息吧。”皋禹走上观星台,为他披上一件外衣。
伯益没有回头,只是轻声问:“皋禹,你说,我接这个位置,是对是错?”
“禹王的选择,不会有错。”
“可是启……”伯益叹了口气,“他回阳城后,虽然表面恭顺,但我总觉得不安。而且各州最近送来的一些报告,也让我担心——青州的铜矿产量突然下降,说是矿洞塌方;徐州的陶器工坊发生火灾,损失惨重;雍州和梁州的边界,又有小规模冲突……这些事单独看都是意外,但集中在这段时间发生,未免太过巧合。”
皋禹神色凝重:“伯益公是怀疑,有人在暗中捣乱?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伯益摇头,“也许只是我多心了。但皋禹,你要做好准备。如果……如果真的发生变故,你要站在正义的一边,而不是我这一边。”
“伯益公何出此言?”
伯益转过身,看着这个年轻人:“我是禹公选定的继承人,但如果我的存在会导致天下分裂,那我的退让就是必要的。记住你祖父的教诲:法律面前,人人平等;天下大事,以民为本。不要因为个人感情,做出错误的判断。”
皋禹深深一揖:“皋禹记住了。”
两人望着星空,良久无言。
深秋的夜空,星河璀璨。但在这璀璨之下,暗流正在汇聚,风暴即将来临。
大禹时代结束了。
一个新的时代,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,正在缓缓拉开帷幕。
而所有人都不知道,这个新时代将以怎样的方式开启,又将走向何方。
唯一确定的是,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动,无人能够阻挡。
发表评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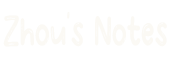





暂时没有评论,来抢沙发吧~